剧情介绍
珍妮(Anne Teyssèdre 饰)是一名哲学老师,一日在宴会上,她与娜塔莎(Florence Dare 饰)相识,也许是因为寂寞,两个本无交集的人成为了朋友。娜塔莎邀请珍妮到自己家里做客,后者欣然前往。娜塔莎有一个奇怪的家庭,父亲离婚,交往了一个年龄和自己相差无几的漂亮女朋友伊芙(Eloïse Bennett 饰),这一点令娜塔莎无法接受,同时,一条项链的失踪也加深了她与“后妈”的隔阂。珍妮的介入让这个家庭里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娜塔莎的父亲显然对知性的珍妮抱有好感,而娜塔莎也渴望能和喜欢的珍妮组成新的家庭。 对于娜塔莎的热情撮合,珍妮显得有些被动,她坚持听从自己内心的感情,不愿掺和到这个复杂的家庭中去。一次四人的乡村度假中,酝酿已久的矛盾终于激发了,娜塔莎同伊芙发生了争吵,而她吃惊的发现自己一直信任的珍妮居然站在敌人的那一边。她该怎么办?在这个春天里,友谊和爱情能否同时播下可以成长的种子呢?陌陌影视陌陌影视樱花影院6080影院故事奶奶2美国队长3情系我心这个医师超麻烦中国刑警803英雄本色我是尼罗好久不见天衣无缝2024狗神2001鸡星当爱情遇上科学家星屑复仇者大象保卫战冷宫女刺客不可思议学园毒咒1985飞翔吧!埼玉2珍妮的婚礼邪密满屋:印度家族集体死亡案护宝联盟第一季行动代号:孙中山雨夜哭无情河畔
长篇影评
1 ) 春天的苹果花开了
2017.11.26 画面很美,春天的花园和房间都很美。开头女主角去男朋友家,没说一句话,长镜头却把情况都交代了,凌乱的床,扔着没洗的衣服,还有食物残渣的餐桌,书籍乱扔的办公书桌,一切凌乱都是那个男人的秩序,没有人在的公寓她不想停留,甚至会以为她是从分手的男友那里拿走自己的东西。
偶然遇到娜塔沙,然后和娜塔沙的父亲,父亲的女友产生交集。四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会提到哲学,台词量非常密集,偏偏还很难听懂。三个成年人,哲学教师让娜,想做文艺评论家的行政父亲,哲学硕士伊芙,你来我往,说的话都是让人去理解台词会耽误看画面的。
让娜第一次遇到娜塔沙就说,不想破坏别人的秩序,后面他她又提到,她讨厌男友的混乱拥挤,但是她对人的自由秩序空间有着暴虐的克制。对男友甚至没那么爱他,但是她计划着两个人以后要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会结婚。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当娜塔沙的父亲出现,她觉得唐突,她破坏了别人的秩序。
表妹住在自己家也一样,保持着礼貌,心底里又克制,自己不破坏别人的秩序,是不是同样不要别人破坏自己的秩序呢?
电影里出现过5处寓所,每处都有很大的书架,这个真叫人羡慕。
2017.11.27 娜塔沙带让娜去度假小屋的楼上,先给了一个空镜头,在房间里面对准上楼楼梯,这个紫藤花的壁纸就这样让人不能忽视,我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国外的碎花壁纸非常常见,为什么我就注意到了这个壁纸的不同。然后娜塔沙和让娜上楼,说这个壁纸是她妈妈弄的,自己不太满意,想要重新弄,让娜表示其实还挺好看,我也觉得挺好看,但是让娜我不知道是出于礼貌或者说是不破坏他人秩序而回应这样中立。
2 ) 如歌的行板
我不爱看电影,尽管有的电影感染我至深,但总体来说不大喜欢。自己也不懂这是为什么,这几天看侯麦,突然明白了。
大多数电影,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讲尽可能完整、尽可能多的故事,所以它就会很赶,节奏很快。一开篇就忙着介绍人物,埋线,推进情节,据说连几秒钟出一个小高潮都有专门研究。看电影成了一种竞赛,一场考试,要留意的东西太多,看不懂就白看了,看懂了还要分好多层次,有时候看完要特意去看分析文章,才能理清脉络,搞懂情节——我不是说电影拍的不好,而是这种状态让人着急,不能好整以暇,觉得自己被放到一个很低的位置上,不知道,不理解。或者被视为弱智,揉开了掰细了讲,或者被视为天才,一眨眼,轻舟已过万重山——考试总是让人紧张。
侯麦的电影,一个人他走,走,走,走上半天,啥也没遇上。一个人他进了一个房间,拿拿书,翻翻外套,洗个澡。两个人出门溜达,一路上尽讲尽讲,路边野花开着,河水流着。两个人争执,一直把话说得透透的,不去留什么伏笔。镜头给的很足,不慌不忙,不赶时间。我常常想,电影里的镜头很珍贵吧,要留给疯狂、流泪、崩溃、甜蜜,它不给流过泪以后,累的睡着了的人的镜头,也不给崩溃过后,一个人变得空洞的镜头——不疯魔不成戏?但是通过镜头,一个人走过海边和山脊,风景是他眼中的风景,他也是风景里的人,这种相互融合,有一种洒脱的味道在里面。我自己是一个喜欢四处游走的人,看到这些简直跟自己走过一样,心旷神怡。
侯麦他从容,演员也用的从容,歇斯底里的情形非常少,你会觉得演员他可能平常就是这个样子待人,这个样子恋爱,这个样子思考的吧。这几部电影看过来,觉得侯麦他戏剧性一点儿也不少,转折一样让人惊奇,可全没有为戏剧而戏剧、为惊人而做惊人之举的行为,这种节奏真的是太棒了,你看不到把控的痕迹,微风过水,自然成纹。
喜欢他电影里的中年人胜过年轻人。年轻人烦恼很多,而中年人,尽管烦恼更多,可是多少已经跟生活对抗过,顺应也顺应的很好,自我也保有的更完整,就是更笃定的样子。所以活得更直接,也更纯粹些。中年人的对话,非常舒服,跟缎子一样。中年人的相处,更加不互相迁就,反而能真正地有朋友。中年人的皱纹,也无忧无虑自然舒心的样子。一生总得有一个阶段拥有从容吧,像河流从山地流到平原,开阔舒展,两岸风景画轴一样缓缓展开。
他的电影,适合人到中年,忙碌,负重,在难得的闲暇里,拾掇一下自己内心,过一个真正午后的时候,看。
3 ) “生活真美好”(La vie est belle!)
娜塔莎佩戴起那串项链,回头发现让娜哭了。一种理解霎时浮现——她是为之前的怀疑感到后悔,愧对娜塔莎和蓝眼睛的男主人,她似乎为良知而哭。其实,至始至终让娜都展现着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带着超然的平和,善于收放情绪,映衬出娜塔莎的孩子气,艾芙的浮躁和男主人的迷狂。让娜的生活最具有表演性质,她的主体意识如此强烈,她的认识如此透僻,却让她不能真正迸发对生活的热情。
但是哲学归哲学,生活归生活。春天的故事就这么发生了,现实里没有复杂的钻营,娜塔莎这样的白日梦者不会成为高明的编剧,一切都是人的情绪,不胜四季撩拨。历史决定论在生活中就是注定要失语的。起初也认定是项链制造情感的失衡点,似乎就是它钩连出几种僭越,几次冲突和一桩未遂的风流韵事。细想后,发现这是一个经典的让娜式的错误。项链是一个愚蠢的符号,本不值得关注。是情感自身的逻辑,比如晚会上两人相似的孤独感制造相遇,男主人的迷人眼睛带来了“三个愿望”的暧昧,项链不会是艾芙偷的故其终将复现(即便未能真的被找到)。谁说心理学是哲学的边缘衍生物?这些法国人总是试图用哲学构筑生活,不过終也枉然,因为或许那暂还不成为生活的核心,生活的向前推动,是由着那些更低级的道理的。
桑塔格说,“思想打破生活的平淡无奇。”这话对她来说不假,毕竟she was not sensitive.然而,一颗东方哲学潜移默化调教下的心灵很容易悟到:是那些无法归纳的道理,或者一经归纳就会显得不是太玄就是太俗的道理完成了生活之美的具象化。让美可感。这未必是侯麦的作品想说的,但没准是让娜最后会感觉到的。
长对话,短音乐,静镜头。除了能引出一些形而上的思考,电影本身也是好的。
概括来说,这是一曲歌唱必然性的智性生活之诗,在表现文化状态上高度有效。影片中各种未被后来之技术遮蔽的人文本真,是在当代的文学和音乐中也罕见的。
4 ) 隐形人
平淡如水的叙述,真实平静的表演,常常给我一种错觉,好似我看的不是故事片,而是外景纪录片,就如同我曾熟悉喜爱的法国二台谈话节目谈天说地(Ca se discute)。后者和大块头尖峰时评及娱乐名人堂之类风格很遥远,主题甄选自百姓琐事,一期专做几个人,包括现场陈述和居家跟踪录影,再来一二佳宾点评。所涉及问题,比如堕胎减肥,两性职场,并无固定的论辩切入点,也不一定解决什么实质问题,好像纯粹集合生态反映,再由此推波给观众瞬间感慨。春天的故事,走到一半也给我类似印象,好似拣到什么拍什么,任何细节都如实再现,同样,记录片里的演员,不需要什么出尘技艺,巴啦巴啦已是真我本尊。
待到尾声,那起项链失窃案终告破解时,我发现我的执念该全盘否掉了,因为若有似无地,片子里确实有说故事吊口味的先机,以项链事件为例,两个女主角冉娜(Jeanne)与娜答莎(Natasha)讨论过甚至模拟了案发现场,娜答莎的爸爸又主动对冉娜提起,最后女生们争执了一场,冉娜又意外拾得项链。总似有条银线光影明灭,时不时轻轻骚动观者的侦察嗅觉,仿若春之柳絮轻扬,抚摩久了,招惹鼻头一个顿悟的大喷嚏。而我也一直跟到收尾再度回荡的春天奏鸣曲,才恍然自己已良久深陷人物无休止的对话,甚至有一点惋叹时间飞逝,怎么就到了终梢,这大约比谈天说地总是高拔了几个层级。
故事里的人物,回顾一下,也绝非来电路人甲,更被赋予了一定的符号涵义。比如冉娜,她有一个中学哲学老师身份,秩序(ordre)、思想(pensée)高频出现在她的口语里。对比她自己和她男友的居所,她的即使暂借给表姊妹,也阳光丰沛,纤尘不染,而男友那边,则由慢镜头告诉我们,是多么邋遢无序。她静静环视之后,去唯一洁净的书桌--那很可能是她工作的地点--抽出两卷书,其一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pure),断开名字,“纯粹理性”,似乎又是冉娜性格的一重注释。她后来偶识音乐学院女孩娜答莎,向她倾诉自己对思考质量的重视,对侵犯平静思索的外因的厌憎。随着两个年轻女子交流深入,冉娜到娜答莎巴黎的家打发周末,她渐渐沁入温暖馨芬的家庭气氛,也距离危险因子--娜答莎的父亲越来越近。可以说,理性是冉娜的坚硬外壳,也可能一直渗透了深层内核,但这并不足以阻止她有高低情绪,她对冲动、激情欲拒还迎。
与她对照,娜答莎父女显然活在另一国里。父亲是文化部官员,离异后风流债络绎,女儿评价他,他非美女莫视,多情似唐璜,他自己的说法是,他不喜欢迂回礼让,更偏好干柴烈火,由着欲望主张(aimer désirer et être désiré)。他和娜答莎一般年龄的艾芙(Eve)交往已久,招致前者强硬的反对。娜答莎,即电影海报上梦幻般的少女,喜欢热烈白日梦,同样一个场景,她和冉娜的解读大相径庭。比如对寡淡的聚会,她以为空坐的冉娜说不准会邂逅白马王子,而冉娜认为概率上远非如此浪漫(beaucoup moin romanesque);又如冉娜对娜答莎的父亲至少口头上并无半分兴趣,娜答莎则显然开始杜撰甚至编排他们的缘分,强调父亲对冉娜的倾心。她白皙纯真的面容下,似燃烧着星光火束,爱与恨皆因微小的风而蔓延燎原。
再一个人物艾芙,则像绷紧情节的火柴,但凡她出现,必定招来娜答莎的迎击。艾芙本人也比较青春张扬,毫不压制自己的表现欲,四个人的餐桌上,她主动挑战冉娜的专业,不断抛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等名士,又频频就康德的“先天”(A Priori),先验论(Méthode Transcendentale)掉书袋,年轻气盛地讽刺以娜答莎为例的大多数人根本分不清“先验的”(transcendental)和“先驱的” (transendant(e))。冉娜见招拆招,像一碗温水一样荡抵对方的剑气,不使唤生硬的书包,不纠缠某个专属名词,娓娓淡淡描述她如何激励学生们改良思维方式。
同一席上,娜答莎表情很丰富,一会儿瞪着眼儿不着四六,被艾芙抢白后尴尬万分,一会儿又因朋友冉娜的落落回应而沾沾自得。她的父亲,静静坐在一边切火腿,一瞬不瞬紧盯冉娜,偶尔插一句观点。候麦设计的对话似乎就是每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日常写照,夹枪带棒都很文雅,话音也不高,可是总有点微妙的吸引力,让人粘在这一桌人物--或者冰火两重对立符号--不动声色拉锯中,挪不开眼。温和的冉娜熠熠生辉,娜答莎与艾芙各怀不同意味的焦灼,而唯一一位男士,垂眸瞬间,兴味已然敛聚。
如此一派自然、节奏舒缓的聊天,几位个性迥异的主角,几处塞纳河畔的房间,就构成了故事的要素。我看到有不堪其冗的观者评价,慢调得仿佛看着青草长出来。我觉得,另一个角度讲,这倒是贴切的比方。电影的主旋律选了贝多芬的春天,春意诱逗着春草萌动,情意滋长,这似乎也是片子所暗示的主题。冉娜和娜答莎初见时,冉娜设问,倘若谁给我吉盖斯魔戒(Anneau de Gygès,见柏拉图理想国)...话就点到这里,未说完的不言而喻:有了魔戒,人便可以隐形,然后听凭欲望,为所欲为。
这个古老的关乎隐形人的隐喻,指环王里各路英豪为之疯狂过,赫.威尔斯笔下的科学怪人曾因此而不可一世,哈利波特披上了隐形袍就可以逃学犯规,闯荡霍格沃茨禁区。在春天的故事里重逢时,我稍觉突兀,随后一再隐现,仿佛这也是候麦想表达的一个中心意思。剧中每个人都有隐秘的欲念,比如冉娜,她眼里的朋友之父,有一对漂亮蓝眼睛,气质诗意,她心里一次次警铃后,依然认可,他看起来不算老梗,她与后者的接触,并非全然被设计,而有一定的自愿,自愿入瓮。又如娜答莎的心事,或纠缠恋父情结,或纯属贪恋家庭的占有欲,父亲和冉娜一而再见面,看似毫无机心的巧合,却也并不可排汰她执拗的红娘欲。
不过这些隐形的小人儿,长势十分徐缓,平衡于人们的皮相面子之下,试探着膨胀,面皮挂不住,尴尬了,就压回来,所以不到一定规模,当事人也不见得感应到他(她)们的爆发力。与之平行的,是那条神秘失踪的隐形项链,它像是为欲望铺路的借口,方便各位主角倾泻情绪。娜答莎因为丢了链子,怀疑并迁怒艾芙,她爸爸则为女儿的乖戾找来一条罪状,那边厢艾芙当然也藏着隐恨,而表面中立的冉娜后来疑心娜答莎和父亲串通起来引诱她,竟也一并怀疑链子事件纯系娜答莎翻云覆雨手。人们日益壮大的失控,到链子无辜复现的时候,才波扑一声干瘪下来,缩回各自理性温顺的壳。
候麦处理隐形人、隐秘的情潮,显得善意而宽容,最后给了所有人回归常轨人伦、娜答莎所谓“生活真美好”(La vie est belle!)的结局或者暂停,诉说的方式--也就是那种给我纪录片的错觉,也和女主角冉娜一般简静低调。他同克罗德.苏提(Claude Sautet)有一点相似,亦即,有时候仅仅通过一个称谓,就能反映人物涌动的感情。苏提的人物,往往经历急速的言辞交锋、感情折磨后,还彬彬有礼互称 “您”。在侯氏春天的故事里,冉娜与彼时尚且陌生的娜答莎聊着聊着就“你”开了,她根本不介意的艾芙,出场第二句就把vous改成tu,而与她短暂亲密,一整日谈话的蓝眼睛男主人,则始终不变敬称。越生分,越松弛随意,不贴心的知己话都无妨派放;越靠拢,却越推拒谨守;不过一定的心门,不确定对方有无诚意,就一直冷冷压抑,直至郁郁内出血。
电影的配乐,也似双生,云雀啾啁,轻舞飞扬,是难得一闻的舒卷贝多芬,后面却垫着大海一般深沉而忧伤的舒曼的晨曦吟唱(le Chant de l'Aude)和他的交响练习曲(l'Etude Symphonique),后者初响时,亲密接触刚刚止步,接着,碎急音符呼应着男女主角的争执小小翻滚,然后他们不再刨根问底,各归其位。如果贝多芬像隐匿的爱火,那么舒曼就是稳下激情的一口凉茶、一张薄网。
当然,春日里的爱,好像仅仅因为发生于春日,也就有了纵容一下的理由,于是,这样的隐形人春游,也自然而然,发乎情,最后止于礼,欲语还休,梦已无痕。
原图文详见:http://ciyunw.blogbus.com/logs/44055031.html
5 ) 三个愿望
人生因为一个拙劣的玩笑持续糟糕透顶得不到任何改变,而真的人生里,这种玩笑又何止千万个。
很感意外的是,让娜的丰厚知识似乎起到了作用,不过最终,是让娜的淡定内敛使得她魅力倍增,超过了年轻娇艳的伊芙。
让娜的聪明使得她放弃了一段她不敢确定和许诺的爱情,她捕捉到并且拒绝了于她不能接受的安排和谎言。不能说这样她就失去了什么,她只是没有得到什么而已。她又回到了属于她的单身公寓里,继续她的哲学教师生涯。
我甚至不怀好意地觉得娜塔莎是恋父情结起的作用,从她找的男朋友的年龄看来,从她对年纪相仿的伊芙的敌意看来。她很像是跟别人抢夺父亲给予的爱感。可能是母亲对她的影响,可能是让娜的个人性格,使得她过分重视让娜,并且希望她和父亲走在一起,这样至少让她比较舒服。
在末段听到了娜塔莎的申诉之后,只能把她的真实意图悬置,表面现象不允许观者探测她的欲求,她本来就是一个易变的女孩子。
整个下来,也就是末段让娜和娜塔莎的较量最为精彩,前面的对话,我老觉得散射到了生活的外面,不是很好。
法国的人文教育真是不一般,可见是有深厚传统的,这也就是影片里人物知识来源和沟通方法的基础。我看到了侯麦的影子。
6 )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Jeanne一直在跟自己对抗。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闯入者,局外人。她拥有两所公寓的钥匙,可是她却无家可归。她与男友的房子一片狼藉,她自己的房间被表妹与男友所占。她只能接受“纯礼貌性的邀请”去一个陌生的派对,一个人无所事事心不在焉得坐着。她甚至希望拥有“吉斯之戒”,变成隐形人。可是,她遇上这个Natacha把她带回家,而她也差点卷入了他们家的风波中。正如舒曼的“黎明之歌”,Jeanne说,这是写给黑夜的歌,而她自己的内心也正在面临着漫漫的黑夜。
Jeanne是这样一个女人,“我对别人的秩序很敏感,我在这方面很讲究”“我很怕碍着别人的事”“我顾及别人的自由,几乎到偏激,甚至是暴虐”,“对于自己的事反而镇定”……
她对自由、对空间到了Natacha家住了她爸爸的房间/沐浴时碰见Natacha的爸爸/回家却不敢用钥匙开门怕打扰表妹/去Natacha的别墅闯进其爸爸与情人的世界……她跟Natacha说:“我是一个闯入者。”她总是有一个局外人的感觉。对于这个世界。她说:“‘三’封密的空间。”她介入了恋父的NatachaNatacha之父的三角关系,聪明如她,怎么可能将自己卷入其中,于是她及时醒来,她说我不做那个外力因素,我不受外力牵引,是自由意志。
当她解开困扰Natacha家的“项链之谜”时,她掉眼泪了。她说:“我总算有点价值了,我不仅是闯入者,不仅是客人。”因为她也解开了自己的心结。她太在乎自由最后失去了自由。可是此刻她也找到了自由。她愿意学着去爱人,去容忍人。其实,我们自己为自己构建起来的秩序有时候就是一道围栏,别人进不来,我们也不愿出去。最后只能内耗致死。
导演给了马蒂斯那张画三段镜头,加起来将近90秒,纯属偶然。有心人不难发现,这部片里包括女主角貌似漫不经心的拿起的书(康德的理性主义)、所听的音乐(舒曼的“黎明之歌”和“交响练习曲”)、鲜花美景都是别出心裁的。最后打出这幅五彩斑斓的画,有水下的珊瑚、海草、小鱼,还有那各在一方的两个造型优美的主角都向我们诉说着女主角所经历的黑夜休止,黎明到来,终于找到了自己,自己与别人合适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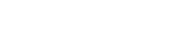




















花已开,料峭春寒,坐于室内火炉旁,他和她升腾起一种情感。尺寸很难把握,但侯麦不愧是大师,感觉电影比小说更具视觉美,更有质感。那个春天的花园真是美翻天。好想自己在那里待着,聊聊天,看看书,喝喝茶,晒太阳,闻花香。音乐里有暗潮涌动,虽然结尾那枯萎的花象征了隐秘的感情。短而美。四星半。
喜欢侯麦的电影,不如说是喜欢着一种生活方式。人是自由的,流动的,无序的,随意的。人具有基本的知识情操,可以自由而深入的思考、了解自己的内心、了解自己的由来,对所在的世界感到疑惑而进行寻找、发现、探寻。人是独立的,是自我的,是自我意识的客观存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在现实里找到这样一种生活很难了,生活过于秩序性,人不再关注问询自己,工作时工作,闲暇时也工作或者靠快捷娱乐来缓释工作的疲惫心情。不再关心自己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要去那里,为什么会爱上谁。秩序是如此的理性化,人成了秩序本身。
本片讲述了人均两三套房的法国年轻人,房子轮着住,不痛不痒的小资生活。
侯麦总能给我情感和道德上舒服的中间值,逻辑自洽、故事简单却讲得异常丰富、完全不必害怕冗长,简短又清晰;巴黎公寓房子的挑高真的有电影里这么高吗?“自由总会退化为暴虐”;“我不会刻意给学生推荐作家,我追求先验性”;侯麦在电影中具像化了依赖直觉和信任先验性的女性的生活与交谈,他质疑信任直觉的人常因为先验性对天真和单纯的怀疑——让娜被娜塔莎丢在枫丹白露的小屋里,与她父亲独处,她在本该尴尬的氛围里因为“证实”了自己的直觉而十分自在,镜头对着娜塔莎的父亲,暗示那条丢失的项链就由这个男人戴着,他因为情况复杂而对情人撒谎,变相坐实了让娜的阴谋论。结尾鞋盒里的项链把娜塔莎从让娜的阴谋论中解救,侯麦借由娜塔莎之口说,你不能凭借想象生活、与人交谈,你要真正地信任他人。
木心说,越是现象复杂的事物本质越简单。侯麦深以为然,所以他的电影永远是两性之间的组合、拆分和搭配。从康德主义者的眼界看来,人总是期待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事物。两个被这种先验判断所困扰的女孩在绿意盎然的《春季》相遇,一见倾心的二者既是同病相怜却也互为镜像和因果。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明显不能帮助从事哲学教育的女主角作出清醒而深刻的自我剖析与自我批判,因此影片需要不断的对话和思辨。当她与女性相处时,她是作为理性(父亲/男友/老师)存在;当她与男性相处时,她是作为感性(女儿/女友/学生)存在。影片在这种视角不断流转切换的驱动下走到两性辩论的高潮阶段,然而二者都想赢得对方的认同,即永远深陷先验主义的怪圈之中。可见西方哲学探讨的核心总是主客关系的对立统一,难怪木心要说中国文化精神的最高境界是欲辩已忘言。
娜塔莎是水,任性无常柔软,一根失而复得的项链就能使其破涕为笑;让娜是土,理智成熟知性,哲学老师的洞察力和绝不妥协的原则;娜塔莎父亲是风,儒雅睿智风度翩翩,在不同年龄的女人面前都能魅力满满;父亲情人是火,热情冲动火爆,有一种随时剑拔弩张的攻击性。春天在哪里?春天在侯麦的人间喜剧中。
首尾呼应的鲜花,却是怒放到凋零再到更换而来,恰比项链的失而复得,绕了一圈回归原点,可这弯弯绕绕里,尽是侯麦的心机和转折,于是,原点业已不只是原点。
春暖花开之时,最适合看侯麦。影片围绕着一场反常而并不复杂的四角关系展开,由谈天闲聊推动情节,以“项链”式的巧合澄清误解,对话中漫溢着微妙暗示与暧昧情感。内敛克制的哲学老师与浪漫狂想的少女,平素感性的人,其实潜藏着理智的一面,看似理性的人,终归亦有受制于情欲之时。侯麦作品中的色彩调配、室内设计与服饰穿搭美得令人叹服。影片里法式中产知识分子的生活世界太使人艳羡了:随处可见书的影子,伴着舒曼的音乐,看看马蒂斯与霍克尼的画作,读读康德、柏拉图和胡塞尔,细细品尝新鲜的番茄,在花草芳菲的庭院中漫步,吮吸春天的味道。PS:对先验/超验/分析与综合判断的餐桌探讨与人物个性隐隐契合,还有对“凡事皆三”的感叹。(8.5/10)
侯麦的故事尺度之小,同比其他故事时会觉得几乎无情节,但用敏感的视角去看又觉得充满张力,戏剧性十足。主人公们保持观察自己对外部世界的真实反应,理解自我,行动并反省行动的意义,为之欢欣、低落 。这些过程散落在日常里,显得矫情又有趣。
两个女孩在party上偶遇,这份偶遇是带点奇迹的,再到邀请去家里住,深夜弹钢琴,对谈如流,这样的开篇是流动的诗,是梦一样的。
特别有魅力的电影,滋味隽永、耐品味。美妙的音乐和配色好像是侯麦标配,不用说了。故事有春天咋临时的暧昧和混沌不明,比如主人公们在人际界限上的试探、探险和防卫。片尾重现的项链恰似迷失而复得的“自己”,但我已不是我,因为毕竟一个新的春天来了。
谈话内容比剧情本身精彩,平淡但不让人觉得无聊,舒曼,柏拉图,康德,胡赛尔,现象学,先验论,属于法国的知识分子传统,这是我爱这个国家的原因。数学不好可以拿出来说,但哲学不可以,哲学不好让人觉得没有思考问题的能力。哲学不是改变你的想法,而是拓展它。尊重艺术与思想,让人羡慕极了。
非常厉害的场面调度,大大超越对侯麦的想象:虽然每个人都很话痨,但却并不让人厌烦,其中充满了令人惊奇的视觉引导。男主角的视线始终在犹疑/游移,几乎从来不去直视,这从根本上揭示了他的内心,而三个女性显然都比他直率太多,也可爱太多。四季故事的一大主题是偶然和宿命,但却比伍迪·艾伦和科恩兄弟有趣得多也乐观得多,以至于让人无法停止傻笑。没错,让人想要继续生活下去的傻笑…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有钱。一个教Philo的老师在巴黎有两套公寓。
春天,春天应该有人告白,有沙发上偶来的倦意,有一次郊游,有友人的离别,有无用的思考。可惜呀,少年只记愁滋味,往时不知春天好。回想已觉浪费了太多,这时就好希望有人开口和我说一句:“其实呀,浪费也是好事一桩。”然后我就能心安理得继续愉快地浪费下去,一直这样惬意下去。
法国郊外的春天花园,真是美得让人流连沉醉。这是四季中最云淡风轻的一部,一切充满了不确定性,也充满了可塑性,让人回味无穷。在春天乍暖还寒的天气里,感情的触碰、试探、亲近、疏远,就像园子里开花的苹果树,枝头吹过的微风,那样自然而细微,春去了无痕。
正如片名一般,全片简单朴素却蕴藏各种各样的生机与未知,三个女孩都与片中的父亲有着或清晰明了或不可言说的联系,你来我往的对话之中几人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在被花草围绕着的乡间别墅中明晰起来,配乐和摄影等电影元素都无太多炫技之嫌却仍让人看后感慨于侯麦对简单纯真生活片段超凡的驾驭和解读能力。
候麦的镜头所对准的永远都是那一群法国知识分子,常看到两三个人就像为了填补配乐的缺失不停说话,却很少有“交流”,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展示。在他们看似闲散惬意的生活,反而上演着难以平息的冲突和波澜,于是,在这些如诗画般美丽的景致中所展开的话题沉重且悲观,揭示着生活的终极无奈。
全片充斥着对白,像那个院子或是找不到的项链,侯麦似乎已经顾不上打理电影里的难以寻觅的视听语言了,仅仅专注于讲一个故事。因此我想借电影的话评价电影:“人们不想打破侯麦的秩序,太费神在其电影的思想上,试图引导自己思考思考本身。”电影井然有序,而我的注意力却混乱不堪;我不断的分神去识别房间里的画册,有戈雅、塞尚、毕加索……我甚至对那只小熊维尼的杯子、还有那扇巨大的拦在路中间的凯旋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电影到底是什么意义,于我已经不重要了、也没必要说了;我只不过是拿着票闯进了这场放映,电影结束我就离开,期待另一部独属于我的“春天的故事”发生。
这个粉白的小女孩,像一条透明线绳一样串起珍珠项链。不论是交谈、争吵还是沉默,我只喜欢有她参与的部分,不理性的,不思辨的,不成熟的,不复杂的,她就是春天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