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遗传了母亲精神病的凯伦(Harriet Andersson 饰)经过入院治疗,被作家父亲大卫(Gunnar Björnstrand 饰)安排到一小岛上调养。凯伦男友马丁(Max von Sydow 饰)是一名医生,两人的感情此时处于低谷,马丁相信凯伦有痊愈的可能。青春期中的弟弟米纳斯颇有才华,但看上去有些焦躁。四人在封闭的岛上休整,但各自心中的不安似乎正慢慢滋长。凯伦发现父亲在冷漠的观察自己病情变化后情绪短暂失控。次日上午马丁与大卫乘小舟离去,被留下的凯伦开始沉溺于冥想,并对米纳斯显示出侵略性,在两人回岛之前凯伦昏倒在破旧的木船内,她向弟弟宣称,自己听到了上帝的声音…… 本片是伯格曼“神之沉默”三部曲的第一部,于1962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陌陌影视陌陌影视樱花影院6080影院科拉多 西拉的到来没说不爱你红粉舵爷野兽家族 第六季沉默法则教皇方济各:言出必行的人通话惊魂千日的约定2024龙年越剧春节晚会都是天使惹的祸命运圣诞玫瑰(国语版)康熙王朝死两次红爪子亲爱的·客栈第三季爱上罗姗纸牌屋第六季超蛙战士豹族刃牙:死囚篇暮光·巴黎缘来缘去1998夺娶隐藏杀手摘下你的面具
长篇影评
1 ) 犹在镜中
《犹在镜中》中讲述了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女儿和她的丈夫、父亲、弟弟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故事主要发生在一个小岛上的与世隔绝的小屋里。对于这个女人来说,她一直在等待着上帝的接待(这被看作一种精神疾病),上帝不仅成为了她心灵上的寄托和追求,同时可以在生理上给予性满足(当然这也被看作某种精神分裂的特征)。而电影结尾上帝以蜘蛛向女人显现最终导致了她精神的完全崩溃。此外,父亲对于女儿的病情并不是特别的关心,他细心的纪录病情的发展只是为了自己写作的需要,女儿的精神失常同他的妻子的自杀好像是一种生命轮回,一种对于他冷漠虚伪的犬儒主义极大的抨击。而她的丈夫只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治疗自己的妻子,他是人类迷信科学的典型代表,因此夫妻两人不可能有任何沟通的信念基础。在整个故事中,最具特征的人物还有弟弟一角,他正处在青春萌动的年纪,对于神秘而美丽的姐姐有一种暧昧的需求,然而由于道德的心理原因,他又对于这带给他冲动的女性抱有一种敌对的态度,他们相互辱骂(在姐姐看到他在拉丁文书中偷藏女人的图片),又相互吸引(姐姐在她的阁楼中向他诉说自己的痛苦)。在电影最后,姐姐被直升飞机带走之后,弟弟在心理上也留下了很深的阴影,他所构建起来的现实生活也因此瓦解。电影结尾,父子一段对话,父亲试图规避上帝存在的问题,将爱作为一种信仰灌输给已经丧失信仰能力儿子。最后一句对白“父亲和我说话了”,也可以看作是整部充满了压抑、挣扎、绝望的电影中一个希望和曙光式的缓和。
2 ) 一切 犹在镜中
—— 《致克林斯人的第一封信》
片头水天相接的幻影,四人欢声笑语不断,快乐的场景完全是一个稳定而有序的假象,海面的波浪,抑或是天空的云朵,二者彼此映衬着不真实,似梦幻。
父亲David(大卫)几乎被置于与女儿Karin(卡琳), 儿子Minus(米诺斯)和女婿Martin(马丁)的对立面,用不断的外出来麻痹自己对女儿病情的认知,想要逃避在小说的世界里,用艺术与现实隔离。晚餐时几句不多的开心话便又言及自己不久将再次离家,一阵克制的争论与沉默交替,David勉强用旅途中带回的礼物分给家人打断这段尴尬,却不敢正视他们的表情,只得用借口悄悄离去,小屋里惶恐不安地走动,禁不住软弱而掩面哭泣。David撑开双臂站立窗前,窗外夜幕宁静,黑暗中的David轮廓清晰,像十字架上救赎人类的基督,而面目和一切细节则被吞噬,唯有独自舔舐内心的虚无。
掩饰过后再次出现的David显得正经自若,立即起身迎上的其余三者则一扫刚才的抱怨,用急于讨好的声音大声宣布这礼物有多么称心如意。
如此刻意的奉迎,越发令人不自在。
儿子Minus极负才华的创作和演出的小剧本《幻想的坟墓》(The Artistic Haunting or The Tomb of Illusions)正是借用了哈姆雷特揭示罪人的方式,在家庭戏剧表演中展现了正在上演的悲剧。Minus扮演的艺术家爱上了来自坟墓旁边的一个声音,幽灵公主要他为爱而放弃生命,可他在拒绝在死亡中去追随她。
生活本就如此。
David麻木的神经被刺痛了,他明白儿子抱怨影射的正是他:用致命的艺术将自己与他人隔绝开来,拒绝交流。但他依然大声称赞,卖力鼓掌。
死亡也许可以获得新生,坦言自杀未遂的David曾在虚无的生活中获得某些莫可名状的东西,也许是对家人的爱。但这一时而起的爱并不足以让他走得更远,当女婿Martin郑重地告诉他Karin的病可能难以治愈时,他一面以亲人的情感难以接受这无情的现实,一面又被小说家的天性所控制,在日记中写道“更可怕的是,我竟如此好奇。我渴望观察她的病情,忠实地记录她是怎样一步步走向崩溃”。
对于精神敏感脆弱的Karin,如此的话语自然是致命一击。空荡荡的阁楼里,一个声音在召唤她,Karin沉迷于幻想,等待着上帝的到来。在她非此即彼的世界里,她要和他们站在一起,放弃丈夫Martin,而Martin一成不变的爱已经无法理解她的内心,在虚无的幻想中,他们渐行渐远——现实与幻想,她只能选择一边,而且她决定了。
直升飞机飞过窗口发出巨大的声音,Karin发出恐惧的叫喊,逃避到墙角。“我吓坏了。门开了,出现在眼前的不是上帝,是蜘蛛!它向我爬来,我看到它的脸,死神一般恐怖的脸,它爬上我的腿,想要进入我的身体,我拼命抵抗……我见到上帝了”,恢复镇定的Karin神色暗淡,看到并明白自己的混乱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不能再往返于两个世界,Karin最终选择了住院治疗。与此同时,David在请求女儿的原谅中,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可怜之处并意欲开始面对现实。
Minus最容易被大家忽视,就像他身上的那条吊脚的裤子一样默显出关爱的缺失。从影片的一开始,他就极力想要证明自己的独立,“做什么由我自己决定”,尽管如此,他依然渴望父爱,想要和父亲谈一谈,一次也好。青春期的性别觉醒和压抑让Minus烦恼不已,姐姐Karin爱抚和精神错乱中的引诱使得成人的现实大门突然间向他敞开。
精神崩溃的Minus对父亲说:“爸爸,我害怕。当我在船舱里抱着Karin的时候,现实突然出现在眼前……这就像是一个梦。一切都会到来,我不能这么生活。”“你可以。但有些事情必须坚持……坚信爱是现实,不管是哪种爱!”“对你来说,上帝和爱是相同的。”“这个想法填充了我灵魂的虚无。于是虚无成为一种财富,绝望变成生命,就好像从死亡那里得到了痛苦的赦免。”
禁忌的打破让Karin与家人分离,却让Minus与父亲的话语交流重新打开。影片的结尾,Minus对着窗外的落日余晖,说道:“爸爸跟我说话了。”
影片中的三个男人角色错位,正如家庭话剧的演出不仅影射了父亲逃避现实的内心世界,还是整个家庭关系的写照。父亲David是高高在上的评论者,可以以罪过之思摧垮Karin的意志也可以坚定Minus的生活信念,而这期间他只能独自品尝现实的悲戚并且逐渐领悟,无论现实如何,终究是必须面对的;丈夫Martin从头至尾都是一个不能全情投入的理智者,他报幕,伴奏,用自己主观的爱情去宣誓,扮演一个如医生般的守护者;弟弟Minus则更趋近于情人的角色,他被自己觉醒的肉欲所吸引,却不能释放,完美的爱情需要死亡的祭奠,现实的生活是残酷和疯狂的。
http://magicdragon.blogbus.com/logs/20338347.html
3 ) 心灵是一面镜子
这种人好像具有“闪灵”一样,生活中的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小段时间,任何一个小场景,对一个敏感都来说,他就像这黑暗中的一面镜子,都能清楚地折射出事物的本质现象。在孤独的小岛,昏暗的午后,平静的水面,看似亲切和睦的四个人,实则内心错综复杂,他们都在为各自的信仰辩护,通过如此尴尬的晚餐(各自心中积累的孤独、责任、埋怨),父亲的礼物(当他发完礼物,立刻伤心地回避,或许这是他承诺他们的,只是没放在心上,匆忙之中,随便了之,他感动了虚伪,无法承受,那又怎样呢,擦干眼泪,晚餐还要继续,微笑还要保持,出来,换成是他们的虚伪的奉承),以及一场家庭小聚会(明明是在鞭笞父亲所坚持的理想、信仰,却以虚伪的掌声随声附和),烘托出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现象,尽管在这最亲的亲人之间,虚伪的外表,空洞的笑声,机械式的掌声,都是在掩饰与保护各自心中的信仰。
卡琳受到了虚无信仰的迷惑根本无法接受马丁世俗的善良。马丁则只是尊行着现世的善良人,对人的内心精神世界漠然无知,所谓的爱只是卡琳这个人,却不知早已失去了她的心。大卫为着自己心中的理想、工作、信仰,冷落了儿子,甚至利用了女儿的病情,观察着她的情况,只为故事研究对象的主题,丧失了人情关怀。青春期中的弟弟彼得遭到了侵犯,“当我在船骸里抱着卡琳的时候,理想被现实破碎了”。麻木的人会随着邪恶利用而不可遏止,当敏感的人发觉那邪恶破坏了心中的美好时,会无法承受,无地自容。从亚当开始,当他吃上知识树果实,身上就存在着恶,当发现身上存在着恶,就躲藏起来,不敢面见神,从此也不能面见神,因为那邪恶,那黑暗在神的光面前必定死去,人会因这邪恶的死而灭亡。大善人阿拉伯的劳伦斯也展示出这一点,当他看到刀子上红通通的血,并非是害怕,而是上瘾,当他发现内心的恶魔,立刻悲痛欲绝地瘫散于地。
影片最后通过父子之间真挚的讨论,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人坚持活着的理由,那是什么?是上帝?是爱?什么是爱?为何总是若有若无?怎么也抓不住?——是啊,你们都深爱着她,用爱包围着她,这跟她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种爱对于她的思想格格不入,难道这就是“上帝”,为何这“上帝”挽救不了她,这只是你们认为的爱,这只是你们心中自私的爱,完全没从客观角度了解她心中的思想,她的内心是那么的孤独,你们各自都只是希望她变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样子,她只是一个木偶一样被看待,当她用真挚的目光盯着马丁,掏出内心深处的话“虽然你总是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到头来一切都是错的”“真正的爱是为所爱的人着想”,期望得到真挚的交流,马丁却以世俗的思想,自私、无情地责问着她“如果是这样说明你不爱我”,难得她掏心掏肺地说出内心的思想,伸手期望得到挽救,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马丁却用冷冰冰的现实一下子把她泼醒,让她留下孤怜怜的心,呆立于现实中无言以对,马丁只是想按世俗的角度,认为她为了他不该再胡思乱想,做一个健健康康的好妻子,他精心地照顾她,只希望她的病尽快得到恢复,做一个世俗的好妻子,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在他看来这是他的责任,这也就是他认为的爱,却完全不了解卡琳的病情,也不愿也不知去深入她的思想,卡琳病了,她就像一个孩子掉入水里那样无助,她身边最亲的人,他的父亲,却是认为她反正无法拯救了,倒不如观察她的思想是怎样一步步地被恶魔吞噬过程,只为成就自己的著作,得名于世。当她伸手期望得到救助,马丁却刚触及到手就急忙缩回,生怕自己也被拉入水中,人一旦触及到自己的利益就拼命地挣扎。
客观,客观很重要,为人处世的原则“想要别人尊重你,你先要尊重别人”前人思想的结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人处世的警钟“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物质的客观只是外在,思想的客观才是本质,主耶稣基督的爱是这客观思想的表现,真理是客观思想的实质,真理的源头是我们天上的父唯一真神,撒旦是那邪恶、黑暗的源头,在真理面前撒旦无计可施,所以,我们唯有纯全的信心藉着客观思想的本质:真理,活出客观思想的表现:主耶稣基督的爱,才能制止撒旦,除去我们身上的罪,回到天上的父的身边。
当我们看到人落入水中,快要淹没,找不到手时,有时,我们需要跳水中,找到她的思想,与她共同思想,共同进退,凭真挚的灵带给她光亮,才能帮助她渐渐摆脱黑暗,当然,前提是你要凭着那灵入住心中,已经学会了游泳,或是带着救生圈,不然你也会被迷惑了,跳下去也无济于事,当然,不会游泳的,一般也不敢跳下去,也不知道怎么去救她,就像马丁一样,只能在岸上干叫。
“我不知道是爱证明了上帝,还是爱本身就是上帝,这种想法,在我空虚的时候拯救了我,空虚变成了财富,绝望变成了希望,就像缓刑,米纳斯,死刑的延期”——思想的深度难以挣脱信仰的枷锁,这连“永恒的敏感者”伯格曼也不例外。
4 ) 大隐电瘾随想
观影感受:肃穆、空旷、孤独、发冷、发抖、哀婉、优美、惊恐

两个世界,实在界与想象界,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同时存在吗?
父亲、丈夫、弟弟,给我一种圣三位一体的联想。仅仅是一种胡乱的感觉,我并不能明确的了解圣三位一体是什么含义。父亲特别像一个假慈悲真自私的旧约上帝,虽然谈不上严厉和去惩罚了犯规的人,但他对女儿的控制是很绝对的。丈夫像一个新约中温和的耶稣,提供陪伴与关爱,但过于理性付出的爱,并不能走进妻子的心里。弟弟则是圣灵,从圣父出来的一位拯救者,最能与姐姐女主共情,提供最真切的帮助。他们三位其实是一体的不同面向,代表着一个故作坚强却脆弱无助,看似理性却难入人心,充满困惑却无能为力的男权状态,或者是一种神权状态。女主是这种状态下的牺牲品,或某种病态的外显者,承担者。吸收并表达了他们不自知的病态,为整个家庭而病。这是一场合谋的悲剧。
那一出剧中剧浓缩了整部电影的核心,13岁的公主原本已死,自恋却不愿付出代价的艺术家用花言巧语哄骗了魂灵的信任,却并没有真正的付出爱。鬼魂经历了第二次背叛,第二次死亡。也许13岁,正是女主母亲去世的年龄,那一刻她继承了母亲的病症,也离自我越来越远,附着在虚伪的父权下,她不断的去索取父亲的爱,却从未真正得到。这份爱充满了自恋与谎言,将她的信任侵蚀,原本的以为是救命稻草,却是经过伪装的致命慢性毒药,一点点的蚕食着她的心。
在船里的两段,父亲与丈夫,姐姐与弟弟。安排在船里,也许代表了某种潜意识,船,让人联想到母体,关于孕育,关于连接,是对女性力量的一种渴望,在母体的孕育中,才能产生真正的连接。船,也让人想到了诺亚方舟,特别是姐姐在上船前忽然之间说会下雨。诺亚方舟正是大雨中的希望,这艘船,现在却如此的破败不堪,姐弟在船里进行了另一个世界的对话,现实世界中则是一种乱伦。他们像偷尝禁果的亚当与夏娃,即是禁忌,也让弟弟体验到了另一个世界。这让弟弟后来会疑问说,回到现实后,我该如何面对生活,该相信什么?父亲和丈夫的对话,则是一种赤裸裸的真相,他们那么肆无忌惮的讨论着对女儿的利用,对妻子病态的厌烦,自大的坦诚,更显可悲。
父亲代表女儿心中的上帝,一个崩坏的上帝。当女主进入癫狂状态,看见原本期待的上帝原来是一只蜘蛛时,镜头给出了父亲高大的背对着女主的影子。蜘蛛想钻进女主的心里,但是不行,女主拼命的挣扎着逃离了,就像父亲宣称自己爱着自己的子女,想要子女相信他,可是,假的就是假的,无论语言多么华丽,感受是诚实的。他只爱自己。蜘蛛吐出网想控制住女主,映射着影片开头父亲和丈夫喜欢的捕鱼,也是撒下网去。我有时会恍惚父亲和丈夫的角色,他们的角色边界感是比较模糊的,丈夫就是女主寻找的另一个同辈的父亲,所以她不能与之发生性关系。
他们生活在一个孤岛上,彼此缺乏沟通与真正的相互理解,各自痛苦着自己的痛苦,每个人都病了。所以,要让人怎么去相信这种无情、混乱、自欺欺人的父性与神权?这是信仰三部曲的第一部,像是抛出了这个问题,上帝已死,人们的信仰应该何去何从?父亲最后回答的爱,也显得那么空洞、虚无与莫名奇妙。
电影中的隐喻和意象特别的丰富,折射出的现象与质疑也特别多,解读见仁见智。它让我最感兴趣的是一种宗教色彩浓重的非传教性表达,提出对宗教对信仰的质疑,是一种深刻的探讨,没有固定答案的追问。怪不得李安这么喜欢伯格曼,他们俩的人生主要议题的内核是一致的,被父亲深深的影响着,害怕着,反抗着,重复着,困惑着。
5 ) 爱和上帝是一体的,上帝就是你身边
又是一个简单的小故事,人物关系很简单,场景很简单,道理也很简单。
爸爸是个小说家,有一儿一女一女婿,妻子死了以后,他逃避责任和失去爱人的悲恸逃到了瑞士。女儿遗传了妈妈的“病”,相信上帝终有一天会降临。影片开始气氛很开心,四个人嬉闹着从海中游泳归来。女儿作为四个人中唯一的一名女性角色,起着调和氛围的作用。她的病情暂时稳定,开始接受家庭治疗。
但是平静之下依旧暗潮汹涌,爸爸和丈夫都知道女主的“病”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作为小说家的爸爸显然对颇有才华的儿子流露出嫉妒,“病情”可能随时复发的女儿,女婿长久压抑不得宣泄的xing欲,青春期的弟弟对姐姐懵懂的情感。一切都在一个暴雨来临的夜晚,在姐姐偷看了父亲的日记之后走向混乱。原来父亲不关心她的病情,她只是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观察女儿的病情,看着一个精神病人走向崩溃。这等的冷酷无情直接击垮了女儿,在混乱中,女儿最终看到了上帝,上帝是一只长了人脸的蜘蛛。上帝并没有治好姐姐的“病”,是一针镇定剂让她冷静下来,她又被拉回到医院。
困惑、恐惧让目睹一切的弟弟几近崩溃,最后他求助于父亲,父亲说是爱是上帝,是各种形式的爱让人摆脱空虚与绝望,让空虚变成了财富,让给你绝望变成希望。单纯的儿子欣喜,上帝一直在姐姐的身边,因为她身边围绕着一群爱她的人。但是姐姐除了弟弟之外,她是否感受到爸爸和丈夫对她的爱呢?虚伪、压抑、克制、以情感流露为耻的两个男人冷酷的可怕。“爸爸和我说话了”,儿子对父爱的渴求简单卑微易于满足,殊不知是爸爸的虚伪和自卑在作祟。
伯格曼在这部影片中表现出对宗教的反抗,对上帝形态的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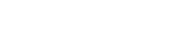




















抑郁的时候不能看这片,痛苦值翻倍,难受到大脑无法工作,可是你看,我不信上帝,这个在影片中所谓爱的具象。而痛苦又都源于丢失了让我们扎根现实面对黑暗的信念,越来越陷入一个怪圈...我宁可自己可以相信某个超出现实的精神寄托,但这些在纯粹而真实的爱面前是多么虚伪且空洞。
这场不知名的疾病是一场梦,是穿墙而过的信仰,而信仰濒临绝望。你信奉什么就能看到什么,故而当你在现实虚幻间游走,看见破碎,看见升空,周身沦丧,不挣脱便沉默,而上帝犹在镜中。我们所在的世界不在于它本身有什么,而在于我们对它的幻想是否磅礴,一切物质的富足皆源自精神的辽阔。
"神之默示"三部曲之首,精妙的室内心理四重奏。令我震慑至极的快速叠化:乱伦序曲-船外V架,暴雨如注,构成光影与声效的双重跳切。以倾斜船舱与龙骨外化扭曲畸变的心灵。墙缝,对门祈祷,亲情冷漠,沉默时的直升机嗡嗡声;上帝是蜘蛛,上帝在爱之中。| 艺术家:世人终将遗忘我,唯有死神疼惜我。(9.0/10)
最难面对的是自己的怯懦,当外界的压力不存在的时候,自己就成为自己最大的监牢。看伯格曼的时候,会觉得疾病和健康并没有真正的分割线。疾病不过是对抗生活中其他更加不愉快的事情的手段。
心中有爱,神即存在。心中无爱,神也无奈。
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这世界到底是温暖的荒凉呢,抑或离开幻象。尽管伯格曼生活一片狼藉,但是如他所说他决定要成为最成功的人,这信念模糊却清晰。
四重奏般的室内剧,法罗群岛,新摄影师Sven Nykvist,巴赫。伯格曼式的特写只在关键情节出现,精致的黑白影调和缜密的剧本。上帝是爱,上帝不在。
8/10。在伯格曼的电影里,爱是拯救人类的唯一力量,但社会文明的发展中造成了爱的缺失,父亲以写作为由产生对责任的逃避,交流只会带来痛苦、误解与谎言,性成为揭示人对被爱与沟通的渴望......结尾女主角似乎重新找到了信仰和方向,但内心疾病的外现却再一次质疑了上帝的存在。
上帝/信仰三部曲之一。充满隐喻和象征的片子。荒凉的岛、破败的度假屋、寂寞的海平面、内心复杂空虚的现代人……伯格曼总是擅长用简单到极致的故事设定来表现复杂到极点的哲学命题。他的演员也总是富于面部表情的表现力,不惧大特写。这电影真的太压抑了。
鏡頭外的導演就是鏡頭內的小說家和父親,觀察記錄一個女人的崩潰過程。所有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抵抗與外人的連接(EVA中的AT Field),即使是至親也不例外,所以才渴望有神明帶領他們穿越與人連接的痛苦和黑暗。父親和神經質的女兒都是伯格曼的精神世界的投射,無論治愈與否,他都在嘗試與自己和解
犹在镜中总体还是悲观的,或者与其说是悲观,不如说是模糊不清的,父亲说爱就是上帝,但他所给予的是一种观察,丈夫给予的是一种体贴,弟弟觊觎的是一种欲望,但对于她的信仰困境,三个人既不理解也没兴趣。可能对破浪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两个人的表述和影像风格是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但内核一致
“有人渴望爱,有人拒绝爱…人生就像梦境,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2018年六月第三遍重看#室内剧,大提琴,对戏剧的热爱,对死亡的探寻,对宗教的质疑,对父亲的诘问,法罗岛上的木屋,所有经典元素集结于此;布光技术一流,光线明灭间的面部特写;黑暗之光,互呈镜面,无法交流永远孤独的主题;伯格曼一生就是一部完整的作品,此片正处于60年代最暴风骤雨的转折期。
最终知晓上帝是爱,或者上帝在爱之中。但这一家四口,却偏生都不懂爱。在各自风雨如晦的角落,彼此试探着逃离或理解,但在很长时间内却徒劳无益。但随着机缘被撬开,各自的开诚布公以争吵、引诱或抚慰呈现,Minus迅速成长,其他人也许霎时老去。黑暗中的镜面,始终穿不透罢。
一个患有妄想症的女人,跟三个最亲近的男人生活。看起来他们对她很好,然而她得不到他们的真正意义上的支撑,还个个以自我为中心,反而需要她来给予支撑。当她无力承担的时候,唯有期待“上帝”降临,来拯救她和三个她爱的男人。只可惜,没有“上帝”,只有蜘蛛——另一个向她索取的对象。
上帝并没有来,上帝始终没来!上帝是一只蜘蛛,上帝是爱?至诚的信仰迷失了希望的光,沦陷在疯狂的泥沼中。
转向室内心理剧的伯格曼,放弃在电影中公开宣认上帝,用蜘蛛代替上帝,在卡琳情绪爆发的那一刻,父亲对自己的冷漠,丈夫与自己失去沟通,自己与弟弟极其矛盾的关系,一切的压抑,都犹在镜中。
发生在[犹在镜中]的角力主要来自于姐弟二人,他们一个代表了向童年、向子宫、向神秘混乱的未知逐步退行的趋势,另一个则经由乱伦而经历了艺术上的逐步成熟。父亲则深陷在无爱的空虚之中。于是在女儿那里这空虚神化为蜘蛛上帝,而在儿子这里父亲终于将爱与上帝并置。这部处理上帝沉默后人类生存状态的第一部曲最终用爱来作为人类悲观境地的一剂缓药,之后的伯格曼作品就不再见到这种圆满的结局了。
以双人特写/近景构成的电影,你会发现大部分时间角色是没有对视的。假若今天仍有电影如此拍摄,这样的表演或者调度是绝不被认可的,因为不会再有电影讨论这样的主题了。“爱即上帝”或许太过抽象,我看到的是男权/神权结构(圣三位一体)下女性的被凝视、牺牲:伪善自私的父亲(圣父)、感性孱弱的丈夫(圣子)、脱胎而又超越于父亲意志的弟弟(圣灵)。戏中戏公主13岁病逝后灵魂被艺术家诱骗,而戏外卡琳13岁时母亲病逝且继承了母亲的精神疾病。若爱即上帝,卡琳苦苦寻求的,就是家庭成员能够给予她的关怀,而作为上帝的实体/代言,男性无一不闪躲回避。最终,经历肉体(与卡琳弃船交合)精神(与父亲深入对谈)洗礼的弟弟,成为了家庭的希望。而结尾被他的头部遮蔽的那轮红日,如被牺牲的千万“女巫”“魔女”,灼目地审视着天国的傲慢与沉默。
又是让自己逼格捉襟见肘的作品。说话与行为方式都缺少生活气息,更多的是文学性与舞台剧化。最后点题,爱即是神,有爱在身边就有上帝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