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长篇影评
1 ) 《诗无尽头》
就我能感到的,这部电影缺乏一些作为艺术品的关键要素——刻意铸就的逻辑性与有力的叙事,它作为艺术品是不够格的,它更像一个梦,而将梦栩栩如生呈现出并不就是艺术——但我喜爱它,是喜爱作为梦的它,而非作为艺术品的它。这似是相当适合以动画的形式展示出的一部电影——其中缤纷的色彩、庞繁却只作为梦景的人与物等等为何不作成动作变化等更完美流畅的动画而要举止不那么合乎“完美”的真人去演呢?不过也许这便是“超现实”与“梦幻”之别——还是要置于“现实”景象中、以“现实”为参照而利用、重组重构“现实”的元素而“超”之,而动画却是自始便立足于“梦幻”的。

这是佐杜罗夫斯基自传电影的第二部,我似乎没什么必要说的。不得不承认它之中的许多情景设置与象征是十分随兴而粗糙的,随兴本是最无刻意的,可过多不加修葺的随兴产物置于艺术之中却显得十分刻意,而某种意义上艺术的技巧本就是通过高超微妙的刻意将那一层随兴看起来的刻意抹隐掉,使艺术整体重新呈示出自然——以刻意达到的(多少是表象的)自然。一往无前、过于无反省的浪漫主义会使心灵感到“尴尬”或被认作矫揉造作,即可如此解释——这也是这部电影的所显露出的吧,或许也是导演自己更重视作品的表达性而不重视作品的观感、将“观众”仅置于第三位的结果吧。

当我发现饰演母亲Sara与初恋Stella的竟是同一人(其实并非很易发现)时,当然也顿感哭笑不得——这当然是含蓄(并不含蓄)地表露恋母情景,“我”与Stella做爱(据两人的恋爱协议,似并非“做爱”?)后情景即切至父亲与母亲做爱、老屋被烧后“我”自废墟中拿出母亲的胸衣:“我的母亲,她一生藏在这件胸衣后,像只谦逊的天鹅,藏身于虚荣的鸭群中……”以及最末的与父亲和解前父子矛盾达到顶峰的码头搏斗,都展示着佐杜罗夫斯基欲展示的自己恨父恋母的俄狄浦斯情节——而《诗与尽头》的整个放逐与回归、抛弃与追寻并行不悖的故事不也似俄狄浦斯的故事么?亚历桑德罗的几次独白所问(问虚空、问自己)的不也正是那斯芬克斯之谜么?“赤裸的处女,将以燃烧的蝴蝶,照亮你的路”——这还是一句诗,而Stella向“我”自述仍是处女、等待山上降下的那个云云这段确实太奇怪了,不过——或许太过度的解释——联系到Stella与“我”母亲的联系,则此处似有将我与处女所生的圣子耶稣相拟的暗示?原谅我想得太多,不过对于诗人,自拟于耶稣、自觉为圣子实在是基本觉悟而已。那么与Stella的恋爱与交合便有上帝使圣母感孕的意味——“我”就是“我”的圣父、“我”的上帝,我在那里生出了我自己——“照亮”了自己作为诗人的“路”。

电影中确实有许多自艺术性看并不必要的东西与显得浮夸的任性表达的情感,但细感细想,佐杜罗夫斯基先生倒确只是将这电影作为给自己的梦,只顾将飘脱于地表的梦淋淋漓漓地表达,哪里顾虑某个“艺术”评价体系的观感,想必他本人是十分陶醉的,又作一次自己青春的幻梦真是何乐不为。片中时常出现的并不很隐蔽的着黑衣黑面罩的人来拿取角色所放下的东西或为角色递去东西以表现得如那东西是漂浮来去之处也更任性明白地显露这不是回忆,不是叙事,而是梦——是梦!以及那些超凡脱俗但似并不很必要的裸露与性描述……处处是梦的元素,处处断续、疏离、任意——惟一的统一在于一切元素所指向的那虚无而实在的“我”……近末处的那游行队伍中红色自然大抵象征生命,而黑色骷髅服自然象征死亡,这是生与死之舞,而涂着恶魔面妆却穿着天使衣装与翅膀的“我”狂饮着自其间穿行而过……片末母亲唱着歌自码头踏步而来,四周是片中“我”所经遇的故人,个个被骷髅环抱俘获,也象征故人都已随“我”远行巴黎而走入死亡与遗忘……

我暂忘记自己还要说些什么了,总之,虽对其任性亦感不满(作为观众都会多少感到被沉浸于自己青春幻梦中的导演所无视的感受吧),但它——在我如今的心境下——仍强烈摇撼着我,无论如何,亚历桑德罗是在真正的活着,那些艺术家们(那位ultrapianist!)是在真正的活着,而我,我也是诗人,我也像“我”那时一样年青,我也想、我也会而且立即就要去过那样的生活。我要和你一起去爱、去热烈地感受、去疯狂地沉思存在、去砸碎欲桎梏它者的一切——礼节、伦常、世故、关系……那些都是死的,可我们还活着。 ——2019.6.7夜毕


2 ) 诗无尽头
你去了法国之后再也没见过他,他死时,你没掉一滴眼泪。但在你的冷漠之下,你的心在说: 爸爸,正因为你什么都没有没给我,你给了我一切。因为你不爱我,你教会了我,爱是绝对的必需品。因为否定上帝,你教会了我去珍爱生命。我原谅你,杰米。 你给了他力量去,忍受这个世界,这个没有诗存在的世界。认清你的爸爸,摘掉他的面具,他不是一个表象。
3 ) 肉身化的魔幻现实主义
《诗无尽头》是佐杜洛夫斯基继《现实之舞》后的第二部自传性电影,这次他将镜头对准小镇马图卡纳和青年时的自己,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方式回溯了自己从逃离家庭至最终逃离祖国的故事。
影片中充斥着大量荒诞性实足的场面与角色,这些对记忆及历史现实的夸张化塑形让《诗无尽头》成为一个广袤且内涵丰富的魔幻现实主义文本。但《诗无尽头》不止于此,佐杜洛夫斯基“属我式”的激情让这部电影又一次成为了魔幻现实主义式的肉身实践——在这里,我认为“魔幻现实主义”一词不再只是一种对于文本风格的描述,而是作为一种创作本体论,进入了自我解谜、自我关照的元叙事范畴。
电影的属我性
让我们从哲学史说起。哲学史,从尼采和克尔凯郭尔为起点,开启了自身的现代性转变。从这时开始,哲学产生了一种内向性趋势——它不关心普遍式的、脱离个体的纯粹思辩,而变成了哲学家主体生命的理性注脚——一言以蔽之,哲学不再外在于哲学家自身。尼采穷尽了一生,发出对自我生命的哲学追寻;克尔凯郭尔则更甚之,它的一生都在询问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到底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而他的哲学竟是不断询问的旅途中的副产物。哲学从这时拥有了一种“属我式”的激情,对哲学家而言,哲学活动不再是进入人类知识共同体的崇高尝试,而是关于自我询问、自我解剖的呢喃细语。
无独有偶,属我式的激情也并不在电影史上缺席。当电影成了一种影像化的记忆,抑或是一种梦境,创作者便被允许通过感官材料的堆叠重新触摸自己的意识深处。就近年来说,卡隆在好莱坞混出名声后,把摄像机转回墨西哥的童年,拍了《罗马》;阿尔莫多瓦则坦诚地给观众献上了自己的“痛苦与荣耀”。而对于佐杜洛夫斯基,这个也许是导演圈中最具有自我情结的文艺导演来说,电影的属我性更是被无限放大。
佐杜洛夫斯基创立了一种叫“心理魔术”(Psychomagic)的精神分析疗法,结合了艺术、东方哲学(尤其禅宗佛教)、神秘主义和现代心理学,去治疗具有情绪问题的病人。他甚至在2019年制作了一部电影(《心理魔术,治愈的艺术》),通过记录与现实中的病人的接触,详细地展示了自己的这套独创的精神分析疗法。他认为电影具有疗愈的功效,先是他自己,其次是他的家人,观众只能是第三位。这意味着,拍摄电影对于佐杜洛夫斯基来说,首要地,并不是一个商业活动,亦不是艺术活动,而只是“面朝自己”罢了。不仅如此,在谈及自己创作电影的初衷时,他说:“我渴望着去打开我们内在深处的自我。为了认识自我,我必须去了解其他人。”因此,在佐杜洛夫斯基看来,电影首先是一种自我疗愈、自我认知的手段,其次才能回归到电影所谓传统的商业和美学价值。在他的词典里,自我永远是第一性的,他人才是第二性的。这种“属我式”的激情贯穿了佐杜洛夫斯基电影创作的始终,并在他的创作后期尤为凸显。目前,他已经完成了两部自传电影的制作(《现实之舞》《诗无尽头》),并在采访中表示“如果只有三百万,我就会继续拍我的自传三部曲,也许会讲述我到了巴黎之后的生活。”
作为实践的魔幻现实主义
在我们厘清了佐杜洛夫斯基电影的“属我性”后,当我们回归到“魔幻现实主义”的话题中,并考察一下《诗无尽头》的元叙事层面,便最终会发现更多玄妙之处。
继《现实之舞》后,佐杜洛夫斯基在《诗无尽头》中再次启用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作为自己影片的主角,大儿子Brontis饰演自己的父亲,而小儿子Adam则饰演自己——此时,自己变成了自己的儿子,而自己的儿子又变成了自己的父亲。在整个荧幕史上,这都是绝无仅有的一例。通过这次荧幕实践,他有意识地创造出了代际的混乱,把我们,更是把他自己引入了一个魔幻的情景中去。他将无有之事铸成了既定的荧幕实践,将隐喻化为了肉身现实。此时,《诗无尽头》这个电影本身,在元叙事层面上,成了一个魔幻现实文本,而把这个文本囊括于自身之中的,便是导演佐杜洛夫斯基的生命本身。于是我们会意识到,魔幻现实主义关照的对象,早已不仅仅是他所创造的文本,更是他自己。事实上,纵观全片,佐杜洛夫斯基就是在干一件事——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视角回溯自己的遭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便不能仅仅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是他的文本创作风格,毋宁说是他认知自我,解构并建构自我的重要方式。正是在此处,魔幻现实主义一词中便有了“属我性”的烙印。“我并不是在谈论自己。”他说,“我是在中和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可以看出,魔幻现实主义真正参与进了他的肉身存在中。它从为民族性、社会性的代言的阶段,最终内化进了个体的无意识中,回归到个体性上,成为实践,成为肉身,成为了个体的一种“属我性”的存在形式。
在智利拍摄本片的过程中,佐杜洛夫斯基联系到了在影片中出现过的关键人物——诗人帕拉。帕拉虽然已是高龄,但思维仍然活跃。佐杜洛夫斯基问他:“如果我还能活24年,你会和我说什么?”随后,在影片中,佐杜洛夫斯基将帕拉的话化作自己口中之词,告诉了年轻的自己。
佐杜洛夫斯基的此在永远是魔幻的此在,佐杜洛夫斯基的现实永远是魔幻的现实。他的生命是他电影的样本,他的电影是他生命的注解。
4 ) The Atheist Mystic, The Dream Realist
Thing is, 事情是这样,关于你的回忆,其实就像你的梦,你会记得,见到过一个如此矮的人,矮到好像长在地里,见到过一个如此高的,好像踩着高跷,要伸长到天上去,你记得你的母亲有歌剧般的嗓音,你的外婆是那么伤心,她的头埋得是那么低,直接砸到了蛋糕上,每当下意识想起暴君般的父亲,他的话语和言说就像一个浮空的巨头,凝视着着火的诗歌,一个喜欢狗的人随时都怀揣着一个狗,一个喜欢跳舞的人永远都踩着舞步,亲吻大量发生,就好像从未发生,你觉得自己长大,你就真的长大,回忆的生机只寄存在你自己身上,他者都被戴上了面具,当你点石成金,世界才开始发生,你的想法才成为你脚下的土地,一场火灾,或者一群奏乐的魔鬼,甚至你如同空气般的缺场,当你成熟,记忆的能力变得发达,或者退化,你记住了更多确切的真实,形体,行为,人,和物,除了没有更新的,更古老的记忆,一切变得与图像和幻觉越来越远,只有图形(figure)勉强暂留。遵循顺势巫术法则的,扭曲的人,物,世界,只有在梦的法则里才具有真实的形体,Jodo,事实上,在试图重建回忆,修建,而不是描绘,事实上,他恨不得告诉你回忆里的每一个细节,是怎么被修建起来,怎么被挂上复古的罩布,如何言出必行。
但是,很遗憾地,jodo确实也逐渐失去了那种图像电影的特质,回忆当然不仅是图像,回忆是故事,是叙述,是告知,是perceived information,而不是received information,回忆的电影捡起了那些电影语言,开始聚焦,开始规划叙事的结构,而不是专注于绘画般的mise-en-scène,它开始展示the making of scenes,以之为开头,而不是结尾,它重新回到了电影,而不是梦,迷幻效果,和图像的世界,从《圣山》到《诗无尽头》,jodo电影从神话的图像和晕影,回到了神话本身。
5 ) 所谓热爱
//对这部电影评价不高的原因主要是,我秉持这样的观点:你说你热爱一个东西,比如诗歌(即便诗歌是所有艺术的王),那你的诗歌里就不应该只是:我要做诗人,我是一个诗人,我要把我的一切献给诗歌诗啊诗啊诗。我更期待这样的态度:我热爱诗歌,所以我的诗歌里有我与我生活的宇宙,我爱诗歌,因为我热爱这个世界,革命动荡与浩劫,花蕊与菩提,都在我的诗里。对于爱人的态度也一样,我很爱这个世界,我也很爱你(诗歌),你(诗歌或其他)是我爱这个世界的一个路径。
风格虽然很新奇,但诗人佐洛夫斯基使用的意像内在饱含的能量并不够巨大。
有的诗人自觉或者不自觉使用的词汇/质料就会有仿佛魔咒般的能力。有个故事讲有个男孩读爱伦坡的著名的重复句“曰,那渡鸦‘永不再’”(“Quoth the Raven ‘Nevermore’”)时诱发了癫痫。我读过某个人诗人读完神曲后写的短诗--我也能从那短诗中感受到神曲的力量。
还有一种正如奥登所说,诗人是使文字产生魔力的人,当他发现了真正有效的符咒时,便迫使不存在的事物进入存在了--create something new。
从这两点看,佐洛夫斯基也不能使人满意。
//最近喜欢的一个17岁小诗人刘佳茵:
哀歌/情歌
这里没有令人向往的溪流和树林
矮木丛里出没的野猫和我们吃同样的东西
同样节奏的生活比如在春夏夜晚发情
同样在秋冬季互相拥抱找地方取暖
而他们能领略音乐中某些我们不知道的成分
可你我都不会羡慕我们满足现在我们有的
一个足够宽敞干净的住所不需要露宿街头
不差的三餐起居舒适一种无聊温馨的小康生活
我们拥有一些姑且称之为知识的东西(姑且称之为知识的东西!
我们拥有的够多可还远远不够
不足矣稳定海平面增长的趋势甚或不足矣让一只将死的猫幸存
不足矣稳定我们的心灵为那片矮木丛(我们的心啊
为与一只猫之间的凝视赋予任何意义
我现在怀疑一切稳固的建筑意识形态
怀疑我正写下的这些象形文字它们为何表示现在他们表示的涵义
原谅我我甚至怀疑你我的爱
我确信爱存在我仅仅怀疑它存在的必要性
我想它不过是人从混沌走向混沌这条苦难之路途中的一声悲鸣......(一声悲鸣!
即便如此,那株矮树丛每年抽出新枝
每年猫儿们在其中生产或死去
每天新生儿的呼号中储存生的信心
每刻受苦者仍在歌唱它们喉头微弱的金色哀歌
而当你我在拥抱中睡去又醒来
又有一声如歌的悲鸣在时间不可逆的轨道里响起...
但愿我们的悲鸣比任何人都更加坚定。
--虽然因为年轻对字句的掌控力不够,但她敏锐的心灵对某些东西却已经察觉到了--我就很喜欢。
//刘小姐致新生儿的歌
幸福,早晨的光,蒙蒙晨雾
笼住你的脑袋,新生儿
玉露流转,你的心跳呼吸
急促,生之渴催醒你,
苏醒的稀疏鸟雀啼鸣
应和你——“生即嚎哭。”你说。
唉请你嚎哭,请坚定
你的声响,愿眼泪明亮你的眼睛
无泪的眼眶只是黯淡
时间的铜钟总在却不永远响荡
愿你所生的片刻闪耀
死神永恒的脊骨将在你的光中震悚。
“生即嚎哭”这一句太好了,首先是一个红脸婴儿刚出生那一刻尖锐的啼哭浮现在脑海,然后预示着人生画卷中无数个哀嚎的时刻--就非常的精确并且高度浓缩。苏轼写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不识愁,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欲断魂,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如果不是遇到了过不去的坎,谁会去求神拜佛,靠自己发现靠不动了,才开始向某些事低头,这样无数的,生即嚎哭的时刻。
6 ) "存在"的困惑与解脱―――从《诗无尽头》看魔幻现实主义
伴随着海鸥的一声声鸣叫,佐渡洛夫斯基一步步迈向了通往未知的船,回首一望,看着那一张张灰白的人像组成的送别队伍渐渐远离,眼中露着倦怠,悲伤,还有,一丝不舍。
就这样,我们跟随着导演开始了自我审视与剖析的旅程,这旅程也许像小佐渡洛夫斯基一样疲惫,像母亲的歌声一样滑稽诡异,像父亲的强权一样使人压抑,但终究我们将完成这一次旅程,终究我们将完成对往阶段自我的自满性解读。
船终究到了圣地亚哥,随着好似话剧中的工作人员的黑衣人将真实的街道一片片覆盖,我们直接被导演从现实拉入了他的"回忆".这种拉入的形式颇具形式感,这种形式感又附加了其内在的含义,一是从直观视觉层面明示了主体(主人公)的主导权,二是明示了这一切就好似那披在建筑物上的广告纸一样虚妄.这简简单单的两分钟情节已然奠定了影片的主基调,"魔幻"的"现实".这就引出了我今天想要探讨的问题,从<诗无尽头>看魔幻现实主义,从魔幻现实主义看"存在",从"存在"看主人公的束缚与解放.
魔幻现实主义作为兴起于拉丁美洲的一种文学流派,与其说映射到了各个艺术领域,不如说其影响着拉丁美洲创作者的潜意识,而如若分析以上问题,必将要从根基开始剖析,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顾名思义,魔幻现实主义是个体提炼现实并将其通过意识精粹并再次外化出的具有夸张效果的现实主义.极端地说,其是艺术家本身根据现实经验而臆想出的现实.而因主流认知问题我们不能极端化,又鉴于其属拉美文化的独特性(当然之后各个国家都发展出属于自身的魔幻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就必然杂糅着拉丁美洲的"乡土情"了,而"乡土情"又往往伴随着与个体相违的一种潜意识习惯,荣格称之为"集体无意识".
"拉丁美洲"作为定义本身就充满着一种政治的压迫感,而这块丰饶的大陆仿佛自古就跟"压迫"与"反抗","梦幻"与"现实"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自公元前三万年至一万五千年亚洲蒙古利亚人种通过尚未断裂的白令海峡陆桥到达这片大陆以来,这片大陆就浸入了一场犹如嚼食古柯叶般的梦境之中,而西班牙人的到来则以像拉丁美洲式断层海岸一样的落差在形式上打破了这可悲的以别的民族的名字命名的种族的美梦,可以说由此开始,魔幻现实主义就已经有了其发展的根基.作为一个独立的大陆,其在享受相对安逸的梦境的同时,当然也缺乏该有的"入世"的政治科学文化的交流与促进,这使得当西班牙的火枪大炮挺进拉丁美洲时,其最先进的文明也只是停留在奴隶制社会而已,而大部分文明只是停留在前阶级社会状态下,而其文明的传递介质也像其大陆本身一样颇具梦幻感,即是各个文明不同的方方正正的原始象形文字,虽有众多史学家辩称"社会制度与文字不能成为衡量文明发达程度的标准",但就当今历史观与结果来看,其文明程度确实有落人之后.但也正是这独特的空间造就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其对于立足于现实的魔幻自古就有独特的创造力,例如颇具神秘色彩的纳卡斯地画,充满隐喻的库库尔坎金字塔,蒂亚瓦纳科的太阳门等等,都是拉丁美洲人民基于力学原理与光学原理制造的世界之奇观,这为如今文艺领域经久不衰的魔幻现实主义打下了坚实的"血缘"基础.而在欧洲人到来后的三百年殖民统治的不断压迫与反抗的斗争途中,无疑又为这基础添加了新"反抗精神""悲剧色彩"的血脉,在当今日渐全球化的社会终究汇集成了如今的魔幻现实.其实我们可以拿辩证法来看魔幻现实,"魔幻"是正题,"现实"是反题,而"魔幻现实"则是合题,它不是魔幻,也不止于现实,它是一种兼具冲击力与感染力的直击心灵的感觉输出,而这种已经高于简简单单的二元论的感受正是每每催人泪下的原因了.这种动人心扉的力量恰恰证明了这种挣扎的悲剧感"存在"于我们的意识当中,这也许是由于不同种民族文化之间的"共相",又或者是称之为人性(我个人向来是不相信的,我认为只有同化),不管其为何,亦不管其在哲学的思辨上是否真实,但就其合理性而言,魔幻现实主义既有其"存在"的多方面合理性了.
"存在",包括物质的存在与意识的存在,包括实体、属性、关系的存在,存在自诞生起就被各方哲学家给予了不同的定义,但基本都涵盖了思维的与物质的两方面,而我以上阐述的"存在"更多的属于思维层面(艺术作品只是外化),而这种思维层面的表述也只是停留在对"存在"于载体本身的思维元素的探讨,亦是超出导演实际掌控的元素(也可以称之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电影的先天表现形式吧),而导演也恰恰在用此载体承载着自己对"自我"与"存在"的思考.
着手于影片的名称《诗无尽头》,这可以是一个论点,也可以是一个态度,如若将其当做是论点,时间的艺术怎么能以空间衡量呢?但若“诗”不是"诗"而是自我的"存在"形式,又如何呢?若此标题是一个态度,又如何呢?
让我们回归电影的回忆,回忆中的
人物总是极具特色的,尽管是路人,其中穿着各异的路人脸上都戴着相同的面具,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阂,而这等环境孤立着感性的主人公,束缚着其情感的释放,而作为主要抒发情感的艺术形式,诗歌无疑是行使反叛权利最优雅又有分量的武器了,这不也正是拉丁美洲人民"反抗精神"的体现吗?影片从未交代主人公缘何喜爱诗歌,但如若我们用辩证法的态度看待其人生,是否可以得到这人与人间的冷漠正是其诗歌爱好的成因呢?而其自我价值又在以诗歌的方式进行实现,是不是可以称之为以诗歌的形式存在呢?接下来的情节恰恰印证了以上观点,主人公的舅舅何塞的忌日上,其母亲悲痛地捏碎那精致的蛋糕,而母亲将舅舅的小提琴传给了主人公,最终被其付之一炬,这不正是意识与精神的“物化”吗?为反叛冷漠诞生的诗的生命再次遇到了阻碍,即是其父亲与家庭,这种家庭的束缚终究使其以砍倒家族树(物化)的外化形式证明了自身精神的"存在",并最终远走,其存在更为完善。而在拒绝同性恋表弟(拒绝社会认知),遇到形形色色艺术家(每一个都在对自身艺术的表现形式进行反叛)后,其诗的生命再次遇到了阻碍与威胁,性的威胁,而性又与安全感紧紧的绑在了一起,在此我们看到了主人公的母性崇拜与归属感的匮乏,在再三被引导最终被掌控(致敬发条橙的性器雕塑被击碎)后,其醒悟到诗的生命冲破层层枷锁而构成的独立“存在”又要再次被奴役,最终其选择了远离,而再次相遇后女友剪去的长发则暗示则无法逃避的妥协。当其夺回自身的主权,并赋予一老一少互相掌控的权利后(给予雕像),其讽刺地获得了允许“存在”存在的特权,并在这个空间内接纳各色生命,其开始有了自我崇拜的趋向(恩里克戴着的镜子),并与情投意合的恩里克结为好友,二人结伴无视社会守则前行,这是自我“存在”的实证,最终二人大开反叛之门。在自我的膨胀并与恩里克的未婚妻缠绵后,其在恩里克的谴责声中明白了,自己已经被同化了,自己已然变成了一个独裁者,自己已然是一个“存在”的赋予者,其经历一段妄自菲薄后,最终与恩里克修好,自我意识回归的同时再次肯定了诗人所必须的人文思想。就在这时,父母赶到称家已被火焚毁,佐渡克洛斯出于个人情绪高兴地狂呼,但当赶到现场后,其才发现,无论什么束缚还是庇护,最终都不过是时空的产物,而时空不再,其“存在”也灰飞烟灭了。在对于存在于时空中的生与死纠结与思考后(红衣与死神的狂欢节),其最终打破了自我的束缚,最终打破了生命对其的束缚,而再次回归了生活。当其回归了生活后却发现,世界终究是实用主义的世界,而自己已再无法在此世界中忍受分毫,最终起决定离开这片土地,前往巴黎,那个言语不通的地方,而在离开前,其最终原谅了自己的父亲(对自身“存在”成因荒谬性的认可,也是对时空的释然)而诗歌也不足以成为其"存在"的全部载体,最终其决定远离这使其"存在"的环境,航向语言不通的巴黎,航向"无"之地
。
通过以上我们不难发现,影片其实是在讲述导演自身的束缚与突破的历程,而这种束缚又恰恰是其体现自身“存在”的外在环境,从个体到社会,从恋母到父权,从意识到肉体,从诞生到死亡,最终,渴求自由的拉丁美洲人民不断突破枷锁,不断向着自由迈进。
就个人而言,魔幻现实主义在本片中的运用仍是颇具特色的,从歌唱的母亲到疯癫的艺术家,从火辣的恋人到内敛的小矮人,其以一种近乎残酷的但又没有悲情色彩的真实穿刺着我们的心,魔幻现实主义的现实在此表露无遗。作为一个反感极端现实主义的观影者,魔幻现实主义兼备了戏剧张力与感染力同时又饱含社会价值,实属当今社会的一个可供现实主义艺术家大展宏图的方向。
最终,佐渡洛夫斯基再次踏上了小船,小船的航向是语言不通的巴黎,其吟着无言的诗歌,看着距自己越来越远的父母与送别群众,眼中闪烁的是,坚毅的光芒。
魔幻存在与否是否重要,就像吸了水却放在永恒日光下的海绵,膨胀与干瘪,只不过是时空的抉择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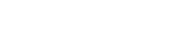




















只看到最后半小时 但是太好了 太好了 热泪
肆意汪洋的色彩,暗蓝如春光乍泄,猩红似瓜纳华托,耄耋之年不输蓬勃激情,在艺术中永生,在诗歌中驰骋。
用无比花哨张扬的方式强调了“我是诗人”,仿佛无比浅显常见的家庭关系也可以无需计较。许多画面具有浓烈的美感,可能是今年HKIFF混剪短片里用上最多画面的一部吧。
帕梅拉·弗洛雷斯一人分饰两角满分!!传记片很容易拍得太实在,这部可以说是充满想象力了。说话像唱歌的母亲,少年舌吻特写,红发巨乳女诗人,走路永远直线的基友,姨妈满腿的侏儒情人,这些都让人难忘,但夸张的舞台剧形式背后又是一个很实在的主题,就是人不断挥别过去走进新生活。
亚历桑德罗是真朋克,撕碎一切。诗是行动,他的行动就是赤诚之诗。
自传体第二部。马戏团/侏儒/小丑/丰乳肥臀的女人,多次验证,佐杜体内确实藏有一个费里尼的灵魂。红发丰腴女人与母亲均为同一人扮演=俄狄浦斯情结。年轻的佐杜与红发女人做爱,交叉剪辑至父亲与母亲做爱。片末与父亲的和解确实升华了整个影片的基调。//你将学会如何快乐的面对死亡。
3.5 有趣的是和同一单元的智利电影《追捕聂鲁达》同样的题材同样的时代同样的结局却完全相反的风格,但文学性却远远没有前者来得深入,被荒诞的调子消解掉不少,导演亲自出现的段落更是让电影变的浅显。不过怎么样说,再做一次自己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梦都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BIFF# 自传三部曲之二,比「现实之舞」更自由:戏剧、剧场、马戏、木偶戏、音乐剧等元素加上超现实主义,呼应诗人的养成。阿多尼斯出镜,恩里克·林、尼卡诺·帕拉等诗人及其他先锋艺术家的影响清晰可见。很多台词赞:『闭嘴,诗人不要解释。』『我把魔鬼交给了灵魂。』
癫狂且童稚的佐老玩了一把自己的“午夜系列”和“魔幻现实”。Not every one can divide the people can be called a poet。only love and hate can make it。the else just making a fuss。只有爱和恨能成就一位诗人,其他的都只是无病呻吟。
又被结局惊艳到了。论剧情冲突『诗』不如『现实之舞』出彩,但『诗』佐杜真正把显微镜放到了自己身上(上一部大部分是在父亲、母亲身上),结构了自己,消解了父权、母权与家。 不说了,佐杜下部片子我也要去众筹一发啊。
老佐继续带领着自己的儿孙逆时而上,扫清家族墓碑上的心之尘魂之憾,最终乘上船,驶向了我们的时代。想继续听其讲述在巴黎的成长心路,因为,老头儿没有给人一丝的过时之感,这种能够与时间洪流近乎完美的融为一体的创作能力,恰恰就是他在强调与追求的所谓看透死亡,便是永生。
嘤嘤嘤 血压又下不来了
本届 HKIFF 看的最嗨的一部片,一部大麻片还很纯瞌完就嗨!诗境与现实交织,连现实都变的不再现实了,好喜欢!所有的外界真相都用最简约的形式投射到了这个并不现实的空间里,走进一家酒吧就能遇到灵魂缪斯,两人一起散着步就能遇到自杀死掉的表哥。融入诗人体内的现实之线。赞!
虽然被结尾感动了,我还是给S分析了半小时这电影为什么不好。一个创作者最糟糕的状态,就是自我感动的状态。一定要自我克制啊。有时候灵感是最容易的,赋予形式是难的。说到想象力,倒是有很多费里尼,伯格曼和Roy Andersson的影子。一个通过艺术自我治愈的例子,也治愈了那些类似经历的人。
有人四十便迟暮,有人八十青春期却刚刚开始。佐杜洛夫斯基恰好是令人艳羡的后者,他的人生故事本身就是一个超现实的魔幻舞台,有那么多澎湃的幻想,和鲜艳的色彩。拉美超现实主义的最后捍卫者,与过去的自己达成和解,让诗歌与电影跳一支激烈的舞然后死去。
诗也有很多种啊。这样高度个人化的lexicon表达出来的才最是诗。伴随开头音乐响起道具组的一众同仁开始狂欢熟悉的佐杜罗夫斯基悄然登场。好像久违的重聚。一直看到片尾字幕出现我自己的名字。年度观影感动。
道理与疯话是两种情感,有情与无情是两套言语。
已经是一部比较克制的佐杜了。但我还是那句话:我爱佐杜和他全家,我爱他们一万年。@London ICA preview
所有道路都是我的路。
自传第二部。希望大神永远健康,把这个系列完成。Q&A环节,大神完全气功师气场,说什么场内都排山倒海,借机索签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