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长篇影评
1 ) 《天意》:创作的真相
作为法国电影新浪潮左岸派的代表导演,阿伦·雷乃向来长于文本的解构,并且能够将极富文学性的文本内容通过带有实验性质的视听语言外化出来,将文学和电影两种媒介紧密贴合,带给人亦真亦幻、虚实叠加的暧昧观感。本片同样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影片的叙述口吻具有极强的文学性,讲述的又恰好是一个小说家进行文学创作的故事,两层文本就这样互为表里,把创作的本质和真相解说得异常通透。 在这个故事里,雷乃无非讲述了一个核心命题,即创作永远代表着一种对于自身的回顾。而且在这回顾的反复动作和持久过程中,一定有一个人或一件事长久地伫立在遥远的记忆深处,让心为之隐隐作痛,想忘不能忘,成为一切矛盾的触发点,成为最疼痛、最深切的刺激。在此基础上,创作者才会为了遗忘,或曰更加隐秘的铭记,而不断出于辩解的目的做出忏悔的姿态,继而构想出一个在伤痛中不断经过历练和美化而最终成形的理想形象,直到把笔下的所有人物都投射成某一阶段或某个截面中的自己,这就是文学创作的内在逻辑。这个故事理解起来着实复杂、凌乱,但最终的意义呈现也着实犀利、精准。 在影片中,雷乃选择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式来直观地展现创作者在角色上的心理自我投射。他让小说中的角色们不断地进行身份嫁接,一边在人物之间构成更丰富的联系,一边深化作为创作者的父亲难以摆脱的执念——逝去的妻子,莫莉。在小说中,起初,克洛德是因母亲莫莉的死而憎恨父亲的独子,后来,这一憎恨父亲的身份由被指认为独生子的伍德福德暂时接替;起初,克洛德的情人海伦只是被形容为“像他的母亲,莫莉”,渐渐地,她的身份开始向上层僭越,终于在和转化后的伍德福德的交流中彻底变成了母亲莫莉。再如,起初,是尚未被指认的伍德福德枪杀了逃窜丛林的作者本人,在小说的结局,同样的情节再次发生,射杀的双方却不同了。这一次,曾经杀了人的伍德福德浑身长毛,又从私生子变成了父亲的化身,成为被射杀的对象,而曾经在法庭中厉声谴责枪杀行为的克洛德则成为了凶手,这时候,他重新回归了那个怨恨父亲的儿子形象。这一次的枪杀才算是完成了作者眼里真正意义上的弑父。这一类身份的连环嫁接在影片中随时发生,时常让人猝不及防,陷入混乱。然而这份混乱与小说之外创作者不断酗酒、自我放逐的颓废相得益彰,反而衍生出一股迷人的朦胧气韵。此外,追溯到身份嫁接的最初环节,我们也会发现,作者其实早已经从各个方面打破了真实世界的伦理设定,让作为母亲替代品的海伦成为大儿子的情妇,又让作为私生子的伍德福德变作大儿媳的情人,这大概也暗合了文学创作的去道德性及其尺度的自由。 如果说小说里故事的结构已经足够奇妙,那么再结合结尾处那段短暂的现实来看,整部影片的表意就更完整也更惊艳了。最后,当现实披露,我们看到作家的晚年生活和他在小说创作中的笔触大相径庭:他的笔触那样荒唐颓丧,他的生活看上去却是无比的光鲜快活。然而,在这幸福的天伦之乐背面,仍隐约可见裂隙的存在:克洛德对父亲的顺从带着卑微的隐忍,而父亲即使在面对儿子们的关怀时也不挑好听的话说,每每让孩子们面露难色。可以说,在这个看似完好的家庭里,母亲一人的缺席已然对家庭的每一个分子造成了隐性的伤害。父亲作为作家,选择把这份潜藏的不快投诸虚假的文学创作,用一种扭曲的方式纾解内心的阵痛。回到现实中重看,好像父亲才是整个故事里最“混蛋”的那个人,而在小说中,其他角色之所以显出或多或少的“恶”,也不过是因为他们被迫地沾染了创作者的原罪而已。但从创作的角度而言,创作者又确乎需要这样一种敏锐的质疑一切的眼光,正如父亲不相信大儿子对自己的恭顺,更不相信他们夫妻的恩爱。对于其他人而言,这也许会被视作阴暗的想法,但对于创作者而言,此番言论的罪责完全可以被开脱。因为,如果他没有这样一种幽暗的,独到的思考的本能,那么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又和真实有何区别?而如此这般风平浪静的真实和暗流汹涌的虚构相比,又谈何魅力呢? 在小说中,已然“成为”母亲的海伦和克洛德说的一句话颇有深意。她问克洛德,自己的到来是否在他的生活中造成了一场危机。显然,她是代表缺位的母亲出现在小说里,出现在小说中克洛德的生命里的。在现实中,父亲始终觉得母亲的缺失造成了克洛德对自己的疏远和冷漠,尽管雷乃对此不置可否。而在虚构的世界里,父亲安排母亲出现,却让她成为所有角色包括克洛德走向毁灭的导火索,我想,这是否也可以看作是父亲对自我的某种安慰呢?他把虚假写得越坏,现实就会被衬托得越好。 创作者或许是幸运的,他们可以把伤痛转化成崇高,把破败点缀成唯美;创作者同时也是不幸的,他们往往于创作的迷雾中走失,不可遏制地,一厢情愿地栖居在自己的想象编织成的圈套里。曾经我们羡慕、崇敬那些故事的创作者,这一次,雷乃却凌驾于其上,说穿了创作者心底的故事,揭晓了他们不为人知的残酷真相。 影片的结尾,孩子们在父亲冷言冷语的驱逐下一一离场,徒留他一人沉醉在生日的宴饮里,这大概也揭示了雷乃创作这部影片的根本意义,正在于让人们知晓,创作这回事尽管带着神圣的光辉,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它仍旧是一片危机丛生、不应随意涉足的禁区。
2 ) 语言的迷宫
《天意》的故事表面看来很简单,不过是这个作家构想中一个关于四角恋情的小说,但是却在主人公潜意识的神出鬼没下刀工斧凿成为对他个人过往的梳理和对的剖析。
小说里那个不靠谱的四角恋情其实不过是:妻子爱上被告,律师丈夫会了旧情人,嫉妒的丈夫杀死了情夫。小说后面的故事却没有那么简单:父亲的冷漠造成了母亲的自杀,童年不幸的儿子与父亲产生了不可弥合的隔阂,最后完成了“弑父”。当然,这只是摆不上台面的潜意识,对应的现实版故事可是光明得多:亲生儿子拥有美满的婚姻,私生子融入家庭,作家父亲写出了本新小说。
小说里的两个男主人公,在作家克利夫的自觉和不自觉中成为他两个儿子,这不仅以相同的名字、相同的演员来“明示”,甚至可以直接从文本中得出。电影在叙述时,旁白的克利夫总是脱口而出将小说里的克洛德喊成“我的儿子”。
死亡是萦绕着这个小说的主题,因为克利夫离死亡这么近。片头出现的濒死的狼人就是克利夫自己——在艾丁顿解剖狼人时,克利夫的旁白说道“哦,他准备划开我的身体!”显然,他把自己带入那个奄奄一息、病入膏肓、快要变成狼人的老人。而长得像他死去妻子莫莉的儿子情妇海伦,一出场就宣告“我快死了”。城市里有大批的人即将变成狼人,即将死去。死亡的气息弥漫着整个城市,弥漫着整部小说,其实也就是弥漫着他那颗恐惧的心。
正因为对于死亡的恐惧,他才流露出对生的向往,对“结实的肌肉、柔软的皮肤”,对人体美的留恋,对美酒所象征的健康人特有的享乐的执着。他通过克洛德的抱怨,道出对自己状况的憎恨:“你是一个亿万富翁(或者以克利夫来说,他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当然也是有钱人),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丧失尊严的方式苟延残喘?!你可以大喊大叫、酗酒、骂骂咧咧地走上黄泉路,人们也许惊讶,但是还能怀着包容心袖手旁观……”事实上这暗示着他的现实处境,他就是在用咒骂和酗酒度过他病痛而尴尬的老年。衰老和病弱是这样一种剥夺人的尊严的窘境,他不得不在写作中停顿下来,愤怒地抱怨肮脏的短裤。它让一个骄傲的男人如此狼狈,以至于他宣泄着对自己的不满。
也正是因为死亡的威胁和老年的孤独感,他对儿子们的态度十分敏感。尽管我们在片尾看到,两个儿子对他十分恭敬顺从,尤其是克洛德,但是克利夫眼里看到的他们并非如此。大儿子因为母亲的死,不可能与他亲近(至少在他想来是如此),小儿子是个后来承认的私生子,总似有些距离。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小说中两个儿子性格的设定。小儿子扮演的伍德福德则体现出柔软的同情心、美好的诗意、与世俗的疏离感,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对死亡的亲近感”。不同于现实生活中大儿子的内向和顺从,在幻想里,克洛德理性、冷漠、富于攻击性。我们可以尝试着不去将他们一一对号入座,那么伍德福德和克洛德是否可以看作是儿子们的现实态和在幻想态中的区别,甚至包含着克利夫自身的部分人格?伍德福德的诗意和克洛德的冷漠、尖锐,并存在这个复杂的老人身。
在克利夫的回忆里,出现了对记忆的分裂的态度:一方面留恋美好的时光,如“海边的阳光,凉爽的葡萄酒,晒得庄重的肤色”,以及笑着对他说“你有你的魅力”的妻子;另一方面,因为对于妻子自杀他所感到的痛苦是如此强烈,他所感到的负疚是如此深埋于心底无法见到阳光,因而他始终在抗拒回忆、拒绝忏悔,但是最终还是服从于内心强烈的愧疚感。
没错,老爷子的心结就是妻子的死亡。在他的梦魇里,他不止一次地假人物之口对此事作出辩解。法庭上的庭辩,伍德福德在回应律师克洛德的步步紧逼和道德审问时说:“我觉得人们有权利选择死亡的理由。”这可以看作是为他自己所作的辩护。克利夫甚至让小说里的伍德福德在广场上贴出横幅:“人们应该有选择死亡的权利。”
而克利夫和妻子的关系也通过克洛德和索尼娅的关系折射出来。因为我们能看到现实中克洛德和索尼娅是非常融洽的一对夫妻,而小说中他们的生活却是平淡至剑拔弩张。克利夫假克洛德之口说,他们的婚姻“处于一种无法言说的倦怠情绪中,我们沉默地呐喊着。……我们僵持着,怎么才能摆脱这种困境?”索尼娅则抱怨丧失自我:“我对你言听计从……我就是依照你的心意造出的一个复制品。”更直接的控诉假借海伦之口说出:“让我告诉你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吧!你父亲就当我根本不存在!他折磨我的方式就是当我是空气,装作不认识我。他在维也纳开讲座的时候,十天里他就不曾把我介绍给任何人。最后一天有人说‘介绍一下你的女伴吧。’他居然瞪着眼睛看着我说‘我不认识她,我根本不知她是谁。’我因羞愤而颤抖!”(此处十分明显,因为镜头立刻切换到克利夫无力地说:‘哦,莫莉,从我的思绪中走开吧。’)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小说里的每一个人都并不特定地、恒定地指代着某一个人,就像海伦可以是濒死的克利夫,也可能成为相貌酷似的莫莉,每个人都随时可以成为这个家庭其中一员的代言人。伍德福德刚刚成为伍德斯的第一幕,他变身成为大儿子,说:“你根本不爱我母亲,你将她一步步逼入绝境。”在餐厅里,伍德福德又突然变身大儿子说:“我想我的人生开端出了问题……有可能是我的童年……”在海边的长廊上,克洛德又变身克利夫,对他的妻子说:“你苦于自己的平庸。”
当这种思想的乱入达到高潮,很快,我们即将看到最有意思的一幕。丈夫拿着手枪干掉了臆想中的情敌伍德福德,但是通过乱窜的潜意识的旁白,我们看到的是,愤怒的亲生儿子干掉了爹地。这个时候,伍德福德变成了狼人(即将死的老人),温情地对克洛德说:“在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是一直爱你的。”这是暴戾的父亲难得的告白。但是没能挡住克洛德的子弹——用子弹来结束两个人的痛苦。
与“弑父”紧紧相连的是“恋母”。片中选择与母亲莫莉相同的演员扮演克洛德的情人海伦是别有用意的。最为明显的是,“儿子”克洛德与“母亲”海伦十指紧扣,成为情人。
“弑父恋母”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最为著名的理论之一,它所指向的是父爱缺失的一种心理环境。我们可以看到在强势、自私、暴戾的克利夫面前,克洛德的人格是受到了极大的压抑的(表现得顺从而黯淡),根源可以想象还有母亲的悲愤离世带给他更大的冲击。把这种性格分析戴上一个故事的面具,我们就得到了“弑父恋母”这样一出经典的隐喻。
至此一个温情脉脉的家庭分崩离析的精神世界已经完全解构。但是,合上书本,我们又回到了阳光下那个美满的温馨的家庭,父慈子孝,琴瑟和谐,事业有成。一个半小时讲了三个故事,雷乃真的是天才横溢!
同样是充满心理分析的意味,但是《天意》和大卫•林奇的《穆赫兰道》以及诺兰的《禁闭岛》有显著不同。后面两部片子的主旨是精神分析,但是这种分析通过隐喻来实现的,而在叙事上仍然保持着相当的连贯性。而雷乃虽然运用了心理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但是他更感兴趣的仍然是叙述手法和结构的实验。在《天意》里,我们看到时空上的参差、人物上的不对应,剧情隐蔽在文学性和自我感极强的叙述中,含糊而又暧昧。事实上,在十年后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中,这种破碎的叙述结构和迷宫一般的剧情更进了一步。
雷乃在电影里使用了一些道具来暗示“此处有玄机”,那就是随时随处可能出现的玻璃酒杯。每当倒上酒,小说中的人物便“突变”成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当海伦在长廊上倒上酒,就开始了对伍德福德的疯狂而尖利的指责(其实是莫莉对克利夫和克洛德的指责);伍德福德在高尔夫球场上莫名其妙地倒上一杯酒,就变成了怨愤的克洛德。这个手法在《穆赫兰道》里,大卫•林奇用的是蓝色的小盒子;在《二次曝光》里,李玉用的是水面。如果今天李玉在电影里用到这个桥段还能让一些人喝彩的话,那么30年前雷乃运用这些手段是多么令人惊叹!
3 ) 一个狡猾的老年共产党员作家和他的恶意幻想世界
这是出不同寻常的戏剧,它有独特的情感和风格,讲述的是一个垂死的,心胸狭隘的,令人生厌的前(?)马克思主义作家,他构思出了一出出牵扯到自己家庭成员的幻想情节。关于电影没有什么好疑惑的地方;很明显Bogarde是这个作家的儿子,Bursty是Bogarde的妻子,且Bogarde的情妇是Gielgud亡妻,即Bogarde的生母(她多年前因患癌症自杀了—但我认为更加可能的是因她嫁给了一个古怪,满口脏话的共产党人,才如此下场,即令她患癌症)。(这个真相)当较晚出场的第四个家庭成员David Warner现身,仅仅在生日午餐现场前几分钟才被揭露出来。
我不知道(电影这样设置)是有意而为之,还是我的主观(读者=客观)接受它,但“天意”有一个收尾的结局扭转,使观众意识到他被老疯子(指作家)的叙述法所愚弄了。 Gielgud的半幻觉式想象故事将Bogarde展现为首要的反派角色,一个极度自负的,缺乏情感和同理心的“伪君子”。讽刺的是,事后显示Bogarde是一个彬彬有礼、心平气和、和善的男人,并且对他父亲和父亲的不洁和怪癖(行为)表现出无限耐心。我们发现Gielgud是家庭成员中唯一一个有着恶毒和自私性格的。其他人似乎都挺好—at least in the presence of his royal Highness the dying scribbler.(这句译不太明白)。
Gielgud饰演一个年老的,幻想破灭的左派人士,他预见性地断言资产阶级是万恶之源—就坐在他的城堡之家,啜饮着昂贵的葡萄酒,仆人紧紧附和着他的奇思怪想,并且他很有可能在瑞士有款额巨大的银行账户。一个富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并不十分罕有;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矛盾,因为它当然不是:铁幕(原意封锁某国家或某集团,后转为某国家或某集团对自己实行铁桶似的禁锢)内外两侧使条款正当化是很常见的事情。然而,如果你认为他对社会主义哲学的核心感到失望,那么请再思考:他只是对“(其他)革命者,而不是革命”本身感到愤怒。因此,在78岁高龄时,这个衰老邪恶的老“知识分子”什么都没学到,徒留无知,准备好逐渐死于无知。这本(或许是廉价的)小说的作者如此荒谬地被骗,他惩罚了他的儿子Bogarde,因他是一个安分守法的,有能力的社会成员。 Gielgud就像所有“空想革命者”一样,他们只是在理论上浅尝辄止并把世界作为他们的极端主义、乌托邦思想和实验的游乐场,他认为他儿子的“资产阶级”是对一个人的能量和潜力的极大浪费。无政府,暴力,暴政和某些人威风作气的思想体系—这些都是作家所信奉的。
在最后一幕中,Gielgud还透露他是唯一一个几乎在所有话语中都使用“F”字眼的(健在的)家庭成员,像某些未开化的,爱酗酒的,殴打妻子的卡车司机。他表现得并不像一个知识分子,因为他像一个沉湎自我的苟延残踹的破烂汽车,一个漫无目的只能呻吟的悲惨的存在,并且贬低别人,或许会死板地创作出一本合乎时宜的小说。他的幻想世界是如此恶心且充满恶意,他令他的亡妻与自己的儿子配成一对。这不仅表明了Gielgud身患恶疾,而且可能在精神上也如此。也许他的身体不是被病毒或癌细胞吞噬掉,而是被自己的邪恶,这是压抑已久的挫败感和自我仇恨所致。 (他从未获得过诺贝尔奖.....呜呼呼。我猜想其他马克思主义作家一定有更好的陈情者,对吧?对于那些不知道的人:百万美元的奖金几乎总是花落左翼作家。我觉得有更糟糕的方式来资助社会主义宣传......)
“天意”有着得体的摄影,相当有趣的对话,以及动听的配乐。电影确实倾向于停留在(作家)幻想部分的末尾:毕竟,人物在电影很早时就已被建立起来,并且在Gielgud最终停止幻想并将我们带入现实世界之前,他只是漫无目的地想到这一点。
阅读Roger Ebert的影评真是太可笑了。这个胖傻子实际发现的是结尾中老人的行为。Ebert根本没有提到任何负面影响,因此我想要搞清楚我们中哪一个真正看懂了电影,哪一个构想了一出幻想版“天意”。也许Ebert在老人的行为中看到了他自己的一些卑劣之处......(好mean惹,所以我好奇这个Ebert到底写了什么??没找到)
这是一部佳作,但从各方面来说又不是很好。我猜,主要的原因是,它在特定圈子中受到高度尊重是因为创作它的这位法国导演(雷乃)—我们都知道他们(导演)是多么无懈可击:经他们之手的东西必然受到我们惊呼“天才!”,带着法国口音。还有个原因是“革命”和“资产阶级”这两个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提及,这通常会令影评人浑身战栗。(xswl)

4 ) 语言实验与家族史
5 ) 《天意》:讲述创作的伟大创作
双(多)层嵌套结构在电影(尤其是近几年的)中屡见不鲜,玩的好的也有许多。如《低俗小说》,将拼贴这一现代文化元素用到了极致;《记忆碎片》,黑色电影色彩的完美融入,电影的颜色象征着不同是时间流向。
此类电影中,被嵌套的大多是“时间”或者“事件”,但在《天意》当中,分层是思考与现实。《天意》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作家晚上于自己脑中构思的一部小说,人物都来自于他的现实生活(本段最大的特色是插入了画外旁白,既让本片带有了一定的喜剧色彩,也清晰地将作家创作的思考过程表现出来)
另一部分是作家一家人在草地上聚餐,此时观众会发现,这些人物和小说人物不仅姓名相同,而且还是同一个演员扮演的。
但是,《天意》非常突出的一点就在于,它现实和小说的人物并非一一对应,而是掺杂了作家的“二次创作”。比如小说中德克博加德所扮演的律师克洛泽(也是现实中作家的儿子),婚姻非常冷淡,二人都移情外人,但是现实中他们的感情很好
其他表现思维的电影中,人物要么是完全一样(如《盗梦空间》中的每个人无论在几层梦境中都是同一个人),要么是完全相反(如《穆赫兰道》中的卡米拉经过戴安梦境的加工后,就成了一个与原本女王般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天意》则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人物性格不相对应,而且小说中映射的人物也是流动的,哪怕他们的扮演者是同一个人!每个人物都只是小说家“一段情绪”的展现
举几个例子
小说:克洛泽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请求法庭判卢克伍德死刑。卢克伍德的罪名是杀死一个向他求死的老人,他在法庭上的辩白说:人人都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力
现实:作家的妻子茉莉由于丈夫对自己长期的忽视而自杀,此时“法庭上的卢克伍德”就是作家本人,他为了不让自己因为前妻的死而愧疚,让小说中人物(恰好由现实中私生子扮演)为自己辩解。而婚生子克洛泽,自然就成了控告他的人
小说:克洛泽的妻子和卢克伍德相爱,二人告诉克洛泽后,克洛泽接了一通来自情人的电话,离开了妻子。见到自己的旧情人海伦后,才知道她已经濒临死亡,“顶对还剩6个月了”
现实:作家的身体状况非常差,于是他通过海伦这个角色来表达他对于自己变老的恐惧,减缓自己所背负的压力。本段的卢克伍德既是他自己又是他的私生子,传达了作家对于自己儿子美好婚姻的嫉妒,在小说中想方设法的想要破坏它。而在后来现实中的午餐里,作家也怀疑过克洛泽的婚姻
小说:第二天早上,克洛泽和妻子一边做饭一边聊天。克洛泽提到自己的父亲,认为“他应当进精神病院”,而妻子刚开始在附和他的话,但是喝下一杯白葡萄酒后,就开始抱怨自己的婚姻
现实:作者对自己的儿子心有愧疚,因此他借小说中克洛泽之口来表达自己的自责。而妻子前半段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不满,而喝下白葡萄酒之后,她就成了莫莉,发泄的是作家对自己行为的反思
小说:克洛泽带着卢克伍德去买衣服,后来又去到旅游公司,让自己的妻子和卢克伍德(现在又在作者的坚持下改名为卢克福)去度假,声称“讨厌卢克福的一切,希望他穿好一点,不要给自己丢脸”,卢克福与克洛泽的妻子在屋檐下谈话
现实:这时的卢克福完全象征了作家自己,他希望被儿子原谅,希望他(哪怕出自嫌弃)优待自己。克洛泽对于父亲的恨又一次被提起,为下一段“杀父”做铺垫。卢克福在屋檐下的谈话,本来拘束,但在喝下白葡萄酒后,又开始喋喋不休的抱怨自己的人生,这也是作家自己的生活
小说:克洛泽带了一把手枪,见到了海伦,后来又来到了森林里,枪杀了卢克福
现实:本段集中体现了克洛泽杀死父亲的心理。前面提到,卢克福在后半段是作家自己的象征,而克洛泽(就是他的儿子)杀死父亲在小说中就成了杀死卢克福。所谓的“杀父娶母”,就完全的在《天意》中体现了出来。海伦的扮演者年龄较大而且旁白也刻意指出“年龄大的可以做他的妈妈”了,而克洛泽在现实中母亲早逝,对母爱的渴望也是他自己的真实情感(但是未到恋母当然地步)。
以上就是小说与现实的故事对应,雷乃的高明之处在于:小说的人物既有现实中人物的一些特征,还有作家对自己的情感剖析与解读,他对于妻子与儿子的愧疚,隐秘的自恋,对爱情和完美婚姻的渴望全部压缩进这部小说中
在阿伦雷乃的电影中,总有可以称为时空标记物的东西出现,如《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中的纸牌游戏和画,《莫里埃尔》中的“杀人回忆”,而在《天意》中,这个标记物就是白葡萄酒。人物一但喝下白葡萄酒,就变身为作家自己,开始吐露真言,现实中,作家在聚会上喝的也是白葡萄酒。作家在小说中借儿子之口说出“父亲喜欢喝白葡萄酒”,从这个解构看来,这也就是打开作家内心的“蓝钥匙”。
当然,本片还有一些有趣的对应 比如小说中克洛泽穿的是黑色西装,而现实中穿的是白色毛衣,相反的颜色象征相反的人物性格
本片还值得一吹的,还有阿伦雷乃的高超镜头,这大大提升了《天意》的趣味和真实度。比如在克洛泽接情人电话的一场戏中,刚开始电话未打来时,就出现的电话的特写镜头,直到电话打来,我们才意识到电话出现的意义。这与前部分作家旁白“找到一个让海伦找到克洛泽的方法”相契合,就展现了人真实的思维状态:想找一个方法用上电话,在脑中几次出现相关画面,后来忽然想到解决方法,才让电话打了进来。雷乃对于这种展现人物思维过程的镜头的极致使用,又一次完成了将人物思维表现在荧幕上的高难度操作
在聚会一段,有一个全景镜头,这首先是告诉观众:杀死卢克福的故事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其次事产生一种喧闹过后的宁静,小说纷杂的杀人案,现实中复杂的家庭关系,在寂寞的林子边发生,环境审视人们,环境包容人们
值得一提的还有演员的表演,德克博加德不动声色的切换状态的演技实在是太好了
《天意》也是雷乃的一次自我剖析,对于艺术创作的重新思考。每一个电影角色都是作者本人,《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女子A,《广岛之恋》的法国演员,乃至莫里埃尔里的海伦和贝尔纳,之前的角色又何尝不是雷乃自我的一面展露?《八部半》是费里尼创作的自我解析,而《天意》是雷乃在戏谑而又不是深刻的讲述艺术创作的过程。
《天意》是雷乃留给世界的又一天才影像!
6 ) 《天意》:如何写就内心和解的自传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6541.html
他一个人坐在凳子上,他一个人看草坪上鲜活的草,他一个人起身,在一个人完成所有动作之后,他通过了那扇门,走进了那间屋子。这是属于克利夫的最后故事,当他告别了庆祝他78岁生日的儿子、儿媳和“私生子”,当他在说完“不要说再见”后喝下最后一杯酒,当他消失于那个进口,死亡便真正降临了,但是在生日这天走向死亡,对于克利夫来说,不是不安,不是害怕,更不是逃避,释然、安然地走向属于自己的死亡,就像完整地写完了自己最新一部小说——身为作家的他,第一次把自己当成了主角,在作者和小说人物的合一中,完成了人生最后的书写。
这是一个光明的结局,但是正如在家人的生日聚会上他们送给他的礼物一样,在走向这个光明而和解的结局之前,克利夫经历了内心复杂的斗争,一件礼物是一把海明威的刀,它不仅是锋利的,而且意味着它将刺向自己的身体,这是“自杀”的象征物;另一件礼物是一本名为《时间的刻度》的书,时间的刻度留在每个人的故事里,它带来的是回忆,而回忆里可能有问心无愧的故事,也可能有闭口不谈的秘密,可能有幸福和快乐,也可能有遗憾和耻辱;第三件礼物则是一架望远镜,它可以让人超越肉眼的局限,望见深邃的宇宙,目光的触及其实是关于自由的一种向往。一把刀指向自杀的痛苦和解脱,一本书带来关于时间的复杂记忆,一架望远镜构筑自由的想象,在克利夫的生日里,这三件礼物似乎在注解他走过的这一生,但是他如何选择面对死亡,则成为了他最后的难题——如同自传的书写,他如何写下关于自己的另一种审视?
光明的结局其实和阴暗的开头构筑了一种对立关系:在仰望高大的树木之后,镜头慢慢平视,之后是一面墙,之后是一盏灯,之后是一间屋子,昏暗的房间里也只有一个人,这是克利夫被疾病折磨而痛苦的写照,他手掌拍打着叫喊:“该死,该死,该死。”在他对死亡的诅咒中,手中的酒杯掉落在地上。从阴暗开始,从破碎开始,从死亡的恐惧开始,以及从一个人的孤独开始,表面上的克利夫是找不到书写新小说的灵感,而实际上就是在把自己当成小说人物的“创作”中陷入对人生的某种不安。如何从这种不安走向最后的和解?如何在“该死”的恐惧中走向和家人的亲切告别?如何用三件生日礼物来回望自己的一生,这是摆在克利夫面前的问题,也是阿伦·雷乃阐述人生自传的一次影像实验。
克利夫慢慢退到了某个角落里,展开的故事是关于儿子克洛德、儿媳索尼娅、私生子伍德福德之间关系的叙事,他只是以“旁白”的方式评论着这些家人的生活和观念,阿伦·雷乃也插入了幽闭在房间里的克利夫的呓语,仿佛他的说话只是为了不被人忘记。很明显,这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种故事场景,克利夫的生活是同质的,孤独的,单一的,而克洛德、索尼娅、伍德福德之间则是隐秘的,矛盾的,复杂的。这是从一个案件开始建立的关系:巡逻队追捕一名嫌疑人,这名嫌疑人是一个老人,当他从树林里逃出来,却遇到了巡逻队一员的伍德福德,老人已经奄奄一息,他恳求伍德福德让他解脱,于是伍德福德用枪打死了他。但是让老人以死亡的方式解脱的伍德福德遭遇了道德和法律的审判,他被认为是杀人凶手,但是按照伍德福德的说法,“他还有其他的痛苦,他正在变成另外的动物——这不是谋杀,人应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伍德福德说老人恳求以死亡的方式寻求解脱,是因为他已经变成了狼人,这是人的异化,死亡可以终结这个异化,但是制造死亡意味着犯罪,于是对于伍德福德的审判变成了关于道德、法律和自由、权利之间的对立。
这种对立当然引出了克洛德和索尼娅,索尼娅是伍德福德的律师,而克洛德则是检察官,为嫌烦辩护的律师和控告嫌烦犯罪的检察官构成了第一种对立,索尼娅认为伍德福德的做法很勇敢,当然也认同他所说对于死亡的自由选择权利;但是克洛德一口咬定伍德福德是杀人犯,而且是巡逻队的一员,巡逻队代表的就是恐怖主义。克洛德和索尼娅、伍德福德在法律意义上构成了第一种对立,他们还在情感层面构筑了第二种对立:索尼娅就是克洛德的妻子,而索尼娅在和伍德福德的接触中爱上了伍德福德,甚至带他来到了自己家里,三个人的矛盾一触即发,旁白声响起:“战斗就要开始了。
索尼娅和伍德福德在一起,他们讨论宇宙,讨论大自然,讨论自由的意义,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有着诗意的一面”,克洛德一进门就向他们发问:“你们完事了吗?”他内心有着嫉妒,但更多是对于所谓道德的捍卫。但是这种表面为情感关系内里是自由和道德的冲突,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立,之后出现了更多也更复杂的元素:索尼娅脱掉衣服的时候,伍德福德却拒绝了她;口口声声说着道德的克洛德却接到了海伦的电话,这个所谓的知识分子、记者正是克洛德的情人,于是他驾车去酒店找海伦;这当然不是这个复杂关系延伸之后的终点,当海伦打开房门面对克洛德的时候,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快要死了。”而克洛德问她的问题竟然是:“你认识一个叫伍德福德的足球运动员吗?他想杀了他兄弟。”而在海伦开门之前,克利夫的旁白抢先说话:“她真像他的母亲。”——难道克洛德的所谓情人就是母亲莫莉?
克利夫抢说的旁白似乎又把复杂的关系网拉向了孤独的自己,在这种退出和进入不断发生的叙事中,阿伦·雷乃其实构建了更加复杂的嵌套结构。一方面是关于谋杀案件引出的多层关系,但是不管在道德层面,还是在法律层面,不管在情感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这是一个关于自由选择和权力束缚的矛盾,克洛德代表的是道德论,索尼娅和伍德福德代表的是自由论;另一方面,在旁白不断插入的叙事中,两种观点带来的对立的矛盾其实是克利夫和克洛德父子之间的“战斗”。克利夫深受疾病的困扰,这是一种身体之痛,他也面临小说创作的瓶颈问题,这是书写之痛,在疾病的折磨和创作的枯竭中,他感受到了不断接近的死亡,他想摆脱死亡的恐惧,但是在以酒浇愁中、拒绝看病的偏执中,死亡反而离他越来越近,但是儿子克洛德对于父亲的死亡恐惧,没有安慰,他甚至嘲讽他,在面对父亲认识30年的医生艾丁顿面前,他直言不讳:“他仍挣扎在死亡边缘,我从未见过在生死边缘徘徊这么久身体却越来越好的人。”而他回给父亲的电报也是充满了指责,于是克利夫的旁白插入进来:“这个伪君子,至少我知道如何活着。”克洛德指责父亲,父亲咒骂儿子,父子之间的这种对立其实依然是道德论和自由论之间的对立。
“我们学会了沉默,学会了控制情绪只为和父亲作对。”这是克洛德在约见了海伦之后在床上和他说的话,而克利夫一个人回忆儿子克洛德在15岁的时候“心事重重言辞浮夸”,“他想发明一种道德语言,它必须绝对是一个逻辑公理。”这就是克洛德所谓的道德观,那时在逻辑公理基础上建立的道德语言,它是必然的,它是固化的,它是不容破坏的。一个只和父亲作对的儿子,一个指责儿子言辞浮夸的父亲,父子之间的对立又重回道德问题,其实揭示的是一段隐秘的故事,“父亲是个淫荡的人。”这是克洛德对自己父亲的评价,为什么克利夫在克洛德看来是淫荡的,因为他认为母亲莫莉的死是父亲一手造成的,是他的背叛杀死了母亲,“她自杀了,无药可救,是他杀了她。”
母亲莫莉是自杀,在克洛德看来背后的凶手是父亲克利夫,这自杀和他杀的界定是不是又回到了伍德福德案件的争论中?那个老人请求一死,是因为他不想痛苦地活着,是因为他将要变成另外的动物,而伍德福德开枪杀死他是不是满足了他的愿望,是不是给予了他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莫莉自杀是不是也是一种自由?因为莫莉在自杀之前已经被诊断除了癌症,自杀对她来说就是一种解脱,那么克利夫即使在道德上有愧于她,也并不是如伍德福德那样的凶手。但是在道德主义者克洛德看来,这是父亲无法免除的罪责,正因此,他并不希望他死去,而是在作对中让他活着。但是这里的复杂关系还在于:克洛德自己有妻子索尼娅,为什么又会和情人海伦约会?在这个意义上,表面上作对的父子在本质上却是同样的人,而这种同质性更像是一种投射——阿伦·雷乃是不是在这里建立起了一种隐喻关系?
重要的线索就在海伦身上,海伦来到克洛德的城市,约克洛德见面,克洛德去酒店按响了门铃,克利夫的旁白是:“她真像他母亲。”海伦变成了莫莉?海伦打开门对克洛德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快要死了。”而这句话对克洛德来说似乎也是耳熟能详,因为母亲莫莉就是这样走向死亡的。情人海伦变身为母亲莫莉,克洛德甚至还问过海伦这样一个问题:“当初我父亲要是娶了你会怎样?”又将情人变成了母亲。如果阿伦·雷乃在这里进行着一种角色的替换,那么在嵌套的结构中,他和父亲其实也完成了一种替换:作为海伦的情人,他难道不是莫莉的爱人?父子从对立走向同一,其实才是阿伦·雷乃在影像中进行的叙事实验:克洛德是克利夫的一种投射,他就是以儿子的身份参与到自己小说的创作中,但这绝不是唯一的角色展现,伍德福德是他的“私生子”,是克洛德的“兄弟”,是索尼娅的情人,当然他也是自己性格的一种投射:伍德的福德曾经对索尼娅就说过:“我的人生开端一定有什么不对,我一直在寻找一种道德语言。”作为私生子,当然渴望道德的归宿,但是他在巡逻队面前拉出的横幅是:“应该让人们以自己选择的方式死去。”他打死老人的理由是:“人应该有自由死亡的权利。”一个把死亡看成是自由选择权利的人,为什么又要回到克洛德的道德论中?
伍德福德就像是克洛德的另一重人格——他们是兄弟,他们和同一个女人索尼娅有关系,他们对死亡有完全对立却源自同一性的观点。而当伍德福德就是克洛德的另一重人格,他们合二为一也就成为了克利夫完整型的人格,所以阿伦·雷乃的叙事实验就有了这个隐秘的线索:儿子克洛德、儿子的妻子索尼娅,儿子的情人海伦,克洛德的兄弟伍德福德、索尼娅的情人伍德福德,都只不过是克利夫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自己所构想的人物,他们复杂的关系也是自己面临死亡的不安、矛盾和害怕使然,当经历了道德上的背叛,当遭遇过人性的矛盾,当参与过巡逻队的暴力,在死亡面前出现分裂的自己,也是克利夫对自我审视的开始,就像那个不断出现的足球运动员戴夫,他是从事优雅运动的人,他一直在路上奔跑,他有个孪生兄弟,而他想要杀死的就是自己的兄弟——这个超现实的意象正是克利夫内心的写照。
所以关于人生是不是有过不道德的行为,是不是需要一种自由的选择,成了克利夫萦绕于内心的最大矛盾,看上去是为了小说创作,实际上是为了书写一部关于人生的自传。78岁的生日,无疑是克利夫走向内心和解的开始,克洛德来了,索尼娅来了,伍德福德来了,他们不再争斗,不再对立,克洛德一直规矩做事,几乎没有什么缺点,也从来没有惹父亲生气;索尼娅认为自己一直活在幸福中;而伍德福德和克洛德一起和小刺猬玩耍,兄弟俩其乐融融——克利夫没有用海明威的刀刺向自己的身体,没有在《时间的刻度》中思念或逃避往事,没有用望远镜遥想自由的宇宙,他面对的是无愧的自己,面对的和解的内心,面对的是可以说“再见”的人生,于是走向那个入口,就是走进人生最后一部小说,就是完成一部自传,就是在人生的超然中读懂“天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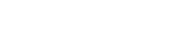




















没办法,男主角不是我那杯茶
7.4/10反正到最后也没能区分出何为现实何为小说,看的蛋疼,文学味过重。另外原版是英文的嘛?
很有意思的构思,看到后来才觉得之前的“虚构”有很多很深的涵义。演员们都很赞,台词有点难懂就是了。。。电影节上映的最新修复版,画质非常不错,不过有细微几处声音还没处理好似的。。
8.5/10,豆瓣标记的第2000部给阿伦雷乃。①醉酒的老人以自己家人为蓝本创作小说,小说的大概内容是婚外情+多角恋+俄狄浦斯情结。本质上是通过虚构作品来反映作家自己的意识与想法。②意识流叙事技法:解说甚至直接改变故事情节的作家第一人称旁白;随意变更的场景与角色视点;混沌的叙事结构(小说创作本身与作者的幻想、回忆混在一起)。③作为主情绪电影:1、多线叙事扣1分(同质于《不散》);2、叙事结构有些复杂不够易懂,导致观众花不少精力理解剧情(=观众感受影像情绪的精力更少),这意味着影像的力量被略削弱,扣0.5。
本片斩获1978年凯撒奖的7项大奖,如此文学化、精妙、暧昧的作者电影,而今却难有与之匹敌者。雷乃将作家一天晚上头脑中的创作历程搬上了银幕,影片就在他的幻想、病痛、回忆和呓语间游移轮转。界限模糊的套层结构,作家的第一人称全知旁白不时充当着评论、提词或直接干预叙事(转场、修改情节)的作用。虚构的角色多次突然忘记自己刚说的话,场景猝然变更,人物也常常无来由地忽聚忽散。虚构故事的内核是婚外情三角恋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故事,并不算复杂,但形式结构上呈现得迷幻而雅致。最后1/5突然切为白日现实,原来几位虚构人物都是作家的亲人,在花园生日宴上相处得融洽和谐,当然,内里曾经的龃龉裂隙或许依然暗自留存。影片由此严肃地探讨了创作过程中的挣扎与曲折、作品与现实经历(虚构角色与人物原型)间的微妙关系。(8.5/10)
英国戏剧碰上法国导演,如果配乐是桑爷的话恐怕就更神奇了(虽然Rozsa的原声已经很好了)。小说中和本人的表演差异非常微妙神奇。不知为何,总觉得如果真拍法国卡司,小儿子的角色非大鼻子莫属。
叙事视角的任意转换,文本内外的随意游弋,雷乃把真实和虚构、确凿和游移拿捏得太好了。
幻象与现实的分离;意识流不是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它本身就存在于生活的每一处。这样富有文学色彩的电影弥足珍贵。
20100818想看
又是David Mercer擅长的心理分析学,又是一部文学样本的经典范例。用假想来把现实、虚幻混淆,用弗洛伊德“永恒三角”框架的颠倒和“弑父”主题去分析前半段,相当过瘾,但结尾又逐一瓦解,令人唏嘘。象征“清白”与“罪恶”的白酒、红酒是重要道具。还是最欣赏大卫.华纳的表演!
单看文本,我还以为是纳博科夫,难怪有人会吐槽雷乃干嘛不写小说偏拍电影,他压根儿就是在用镜头和音声在写作嘛。
了不起的雷乃,在对电影语言的革新和电影形式上的探索方面总能轻而易举地将其同行远远甩在身后。4星半
蛮厉害的,但用电影做这样的创作似乎不如用小说做同类创作好看?还有就是,老人的创作内容有股子缺乏幽默感的老人味道,吓人,可能只怪我怕绝症片。那个时候David Warner还能挤进这种级别的卡司哦。
属于近期看过的最佳电影。电影中有一个奇怪的叙述者,电影也按照他的设想一步步发展,时而是简单的喃喃自语,时而是繁杂的难以捉摸。雷乃也创造了一种暧昧的叙事方法,其中不乏艰涩的片段和断裂的剧情。再者,抛开此片的叙事方法,单单就故事而言,是一个美妙的观影经历。
前半段大概只是觉得有趣,中后段便觉得太多东西要想,完全被启发。Dirk Bogarde的表演既有个人特色又那么切合主题。从树开始,“生命是部小说”里的树是童话世界,所有故事都从那里引申、幻想出来。
雷乃最复杂,最危险的一部作品。表面上看这里有两个故事:真实的,关于作家将死之际的疯狂,以及虚幻的,作家脑海里的一部半自传小说的再现。但是雷乃将这两条线索以极其复杂地方式编织在了一起,令观众始终处在不稳,困惑与矛盾之中。即便观众自认为已梳理清一切,结局也自会证明:真实从未存在。
小说体性质的电影艺术被阿伦·雷乃发挥到极致,利用摄像机这个写作工具制造出「语言的困境」,在他的电影中,作者意识高于一切外在因素,看着看着,就会连现实与虚幻、主观与客观、融入与超脱、自我与他人的区别都被混淆不清,而这些问题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思考,需要冷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
note:http://blog.roodo.com/esaurimento/archives/13588103.html
确实像德娄的戏剧,每个人物出场都带着自己的背景故事。想象渐乱,现实侵入虚构,午夜的想象和醒来的晴天丽日对照,才显出心底无法摆脱的多疑和歉疚。最吸引人的还是Bogarde,他太适合演这种极尽讽刺挖苦的角色了,右眉毛抖动的小动作特别邪恶。
令人又愛又恨的一部電影呀。整部電影就是Bogarde跟Gielgud的英文講的不清不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