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故事改编自乔纳森·雷蒙德的小说《半条命》,雷蒙德和导演雷查德共同改编,设定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即1820s)的俄勒冈,一个西方厨子Cookie(约翰·马加罗饰演)来到荒蛮的西部碰运气,遇到了同样前来寻找机会的中国移民King Lu( 奥瑞恩·李饰演),两人一见如故,并借着一头奶牛合伙做起了生 意。陌陌影视陌陌影视樱花影院6080影院洛城夜巡宝妈时光里死亡笔记3卡戴珊家族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顽皮鬼2十八,十九爱能给别人吗盗日英雄传摩纳哥女孩消失文明的编年史心动的信号第五季甜木兰第三季特别市民一路逆风佛都有火村庄一个美国女孩的故事-玛莉琳1955:非凡的圣诞节鸳鸯绑匪村官不难当永别了傻瓜2013虚拟人生在路上马卡里奧蛇蝎夜合花
长篇影评
1 ) 《第一头牛》截图&初涉Peter Hutton



















"Hutton's exquisite images, precise, observational style, and use of long takes and silence encourage the mind to roam. These ships come to seem like inspiriting physical measures of mankind's outsized capacity for hard work and boundless imagination, by which we overcome the isolation of the human condition." - Film Comment
彼得·赫顿(Peter Hutton,1944 年生,底特律)是电影中最热情、最富有诗意的城市和风景肖像画家之一。作为一名前商船海员,他花了近 40 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航行,经常乘坐货船,对从长江到波兰工业城市罗兹以及从冰岛北部到孟加拉国海岸的一个船墓地。这18部电影的全面回顾展示了一位艺术家致力于唤醒一种更加沉思和自发的观察和想象世界的方式。
无论是追忆一座城市的逝去,还是反思大自然的瞬息万变,Hutton 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雕刻;每部电影都在无声的遐想中展开,从固定位置拍摄的一系列扩展单镜头,让人回想起电影的起源以及绘画和静态摄影的传统。展出的作品包括赫顿在 1970 年代开始的两个宏伟系列——一个是纽约的印象派速写本,另一个是对哈德逊河谷的探索,以托马斯科尔和 19 世纪的方式转录和提升景观发光主义画家。“就像芭蕉的俳句,”学者汤姆·冈宁 (Tom Gunning) 观察到,“这些看似简单的电影提供了观看和塑造图像艺术的课程,让你想知道如何有人能同时制作出如此谦逊和如此惊人的东西。”
引用: //www.moma.org/calendar/film/600 //expcinema.org/site/en/wiki/artist/peter-hutton
文章: Peter Hutton, Filmmaker With Austerely Romantic Worldview, Dies at 71
2 ) 这部有魔力的“新”电影,祭出年度最美结尾
晨间的郊外,一只黑狗在泥地上漫无目的地嗅探,相隔不远处的女人则捡拾摆弄着石子,画面恬静怡人。没过多久,黑狗似乎嗅到了什么,不停地摇摆着尾巴。
跟在黑狗后面的女人发现情况后随即将黑狗轰到一旁,她拨开松软的泥土,发现早已化骨的头颅。她继续小心翼翼刨土,直到两具完整的白骨映入眼帘。

这是当代最重要的女性导演之一凯莉·雷查德的新片《第一头牛》的开场段落。这部年初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美国另类西部片,向观众展示了19世纪初西进运动时期两位男性的特殊友谊和破碎的美国梦。

影片《第一头牛》改编自作家乔纳森·雷蒙德的小说原著《半条命》。跟凯莉·雷查德此前的六部长片一样,该片在受众上仍旧局限于钟爱独立电影的那类影迷群体,同时也仍旧获得影评人和电影媒体一致的褒奖。

雷查德没有在具备权威影响力的影展上拿到过重要奖项,但这并不妨碍她在电影评论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之所以如此,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回到她的创作中寻找。
紧接着《第一头牛》中两具白骨的亮相,下一个镜头将观众带回到了19世纪20年代,摄影机对准一个灰头土脸的年轻人的身体和面孔。这个年轻人本名为Otis Figowitz,由于他负责为同行的人做厨,别人习惯性地戏称他为Cookie。

Cookie是美国西进运动中渴求获得财富机会的千万个迁徙者中并不算起眼的一员,并将注定淹没于历史长河中。生于马里兰州的他命途多舛,父母相继离世导致他从小就过着一种居无定所的生活,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他去牵挂的。

某个晚上,Cookie在丛林深处发现了饥肠辘辘且一丝不挂的King Lu。King Lu是来自中国的移民,他之所以会是这副狼狈的模样,是因为他正被俄罗斯人追杀。

善良的Cookie给King Lu送来了食物和遮身用的毯子,搞清楚King Lu的遭遇后,Cookie决定帮他一把。这是Cookie和King Lu的第一次相遇,不久俩人便分开了。

经过长途跋涉,Cookie一行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在这里他与其他人分道扬镳,或者更确切地讲,他被同行的人抛下了。来到酒吧休憩的Cookie与King Lu再度遇到,俩人在King Lu的小木屋里交谈甚欢,一来二去彼此变得前所未有的亲近。

此地的首领Factor从远方订了两头成年奶牛和一头小牛,但运到这里的时候,只有成年母牛最终撑了下来,她便是该地区的第一头牛。King Lu想靠油煎饼赚钱,但他需要这头母牛的奶来提升饼的风味,Cookie与King Lu商量后决定夜间去偷奶。

饼的反响超乎意料的好,以至于连续多天供不应求。看着眼前巨大的商机,俩人有些忘乎所以,他们频繁地半夜去盗母牛的奶,以为能就此走向致富的道路,但不料秘密很快被暴露。
为躲避Factor手下的追杀,King Lu在逃亡中跳进河里,碍于胆量的Cookie躲进植被茂密的隐蔽处,俩人再度走散……

资本主义与一个国家的诞生
显然,《第一头牛》是一部关于资本主义精神与美国拓荒史的电影,雷查德在接受相关的媒体采访时,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影片与资本主义的直接联系。不管是Factor所代表的一个地区的旧资本,还是King Lu和Cookie作为商贩的新资本力量,他们在象征意义上都是一个资本主义市场模型的一部分。

作为历史和文化建成并不久远的移民国家,美国的诞生包含某种与生俱来的暴力和疏离感,这在影片中那些保持沉默的印第安土著,尤其是印第安女性身上得以微妙的体现。而作为中国来的移民,King Lu被俄罗斯人追杀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美国的移民政治的反映。

某种意义上,“美国梦”是西进运动中驱使着人们走向进一步屠杀印第安人的导火线。但雷查德并没有试图就美洲大陆的移民与土著间反主为奴的殖民主义历史进行宏大的解构,她反而轻巧地将这个背景注入两个移民主人公的宿命之中,让他们以追逐“美国梦”的失败近距离破除“美国梦”的虚假。

女性视角下的男性与男性暧昧
在雷查德的电影里,五大三粗的、硬汉化的男性形象是永恒缺席的,在雷查德对人物的审美取向里面,她更青睐于那些敏感的、看起来羸弱的或是不那么性感的男性形象。这在雷查德此前以男性为关注核心的电影《昨日欢愉》,以及涉及了重要男性角色的《夜色行动》中已经展露无遗。


从以上的角度来讲,雷查德电影里的男性实际上是一种刻板的男性气质在女性视角干预下的性别消失,因而男女两性的情绪的表达逻辑和气质的美感是非常接近的。这就不难怪梅尔·梅洛的短篇小说《贝斯·戴维斯》中的男性主人公,为什么会摇身一变成为了凯莉·雷查德《某种女人》里的女性。

正如片头对威廉·布莱克《地狱箴言》中那句“鸟筑巢,蛛织网,人结友”的引用,影片《第一头牛》是一部讲述了“人结友”的电影,Cookie和King Lu的关系也的确属于男性正常的友谊范畴。但将这种关系纯粹归于友谊,又毫无疑问是粗暴的。

雷查德并不反对观众对两位主人公任何具有合理性的遐想,哪怕认为他们是情人,在雷查德看来也是可行的。
何况人物的“暧昧”甚至并不表示人物之间必须具备某种已经确定的关系,“暧昧”体现在《第一头牛》中即是一种潜在的依赖感,一如电影开场的两具靠近而栖的白骨所给予观众的意境。

西部叙事与公路叙事
在雷查德迄今为止的七部导演长片中,她都或多或少地接洽着两种固定主题的叙事,即西部叙事和公路叙事。我们能毫不费力地便在雷查德任何一部电影里发现这两种叙事的存在。

凯莉·雷查德的西部叙事,是地理背景、历史构想和美学层面的一种综合。《第一头牛》的“西部”是希望与死亡同在的俄勒冈,《米克的近路》的“西部”是危险的蛮荒之境,《温蒂和露茜》和《某种女人》的“西部”是无人注视的偏僻小镇,《昨日欢愉》中的“西部”则是一种远离现代的手段……
西部,作为一种符号无时无刻地侵蚀人物,因而雷查德电影里的人大都带有西部人的特色,他们看起来疲惫、迷惘和无聊。


谈到雷查德的公路叙事,不得不重点提及雷查德电影中可能是最重要的主题:漂泊流浪(Drifting的表意更准确)。从处女作《野草蔓生》到《第一头牛》,雷查德电影的主人公几乎都处在一种离家的状态,这种与上世纪嬉皮士运动一定程度上接轨的“在路上”精神,成为了人物自我实现的一种外化的形式。

影片《第一头牛》贡献了今年新片中最美的结尾:拖着疲惫的身影逃命的Cookie和King Lu最终抵挡不住睡意,他们在丛林中相继闭上了双眼。

电影并没有将后续的情节告知观众,但作为观众的我们都知道,未来的两具白骨便是此刻陷入睡梦中的他们。只不过我们仍旧会被雷查德的处理所打动,我们仍旧抱着这样的期待:希望他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危险已经悄然离开。

作者| 多尼达克;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3 ) 一个中国人在美洲的故事
导演挺坏的,她在影片一开始就剧透了。通过开篇的“鸟有巢,蜘蛛有网,人有情”一句话让观众知晓了影片主题(这是一个关于友情的故事)。接着两具尸骨的出现,让观众知道了主人公的结局(俩人一起死了)。然后,她开始讲故事。
一个关于我---一个中国人在美洲的故事。
我叫陆金,出生在中国北方,9岁的时候来到广州,后来我跟着一帮英国商人去了伦敦,我离开中国的时候还是清朝的嘉庆皇帝在位。到了伦敦没多久,我就把辫子给剪了。中国古话说入乡随俗,我开始按着洋人的方式穿衣行事,还学会了讲洋文。在英国呆了几年我去了非洲,然后是美洲。我和几个俄国人来到俄勒冈寻找发财的机会。有天俄国人怀疑我的一个同伴偷了他的东西,他们把他分尸了,我开枪打了其中一个俄国人,然后就跑了。俄国人一直在追我,我把衣服脱了,枪也扔了。又累又饿实在跑不动的我藏在灌木丛里,就那样,被厨子发现了狼狈不堪的我。
厨子是个好人,他让我住在他的帐篷里过夜,给我盖上他的毯子。第二天天刚亮我就醒了,继续逃亡。过了一阵子,在镇上唯一的小酒馆里,我又遇到了厨子。当时我正坐在酒馆里跟人玩象棋,顺便赢点钱。有几个无聊的家伙开始找茬儿打架,掌柜的锁上钱匣子也出去看热闹了。厨子一个人在吧台上替打架的看着一个小婴儿。酒馆里就剩我俩了,我叫他,他回头,认出了我。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厨子算是我的救命恩人。我邀请他去我的木屋坐坐喝点酒。回家的路上,我看到在我早上搭的小机关里刚好捕到一只猎物,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动物,介于兔子和田鼠之间。美洲大陆是片富饶的土地,有很多我从未见过的东西,尚未命名的东西,这片土地有待开垦,希望这次我来的足够早,新来的人可以在这片土地上自己制定规则。
到家后我开始劈柴烧火准备做饭。我让厨子坐着休息,可他不肯闲着,拿起苕帚开始给我打扫房间,等我劈完柴进屋,厨子在一个空瓶子里还插上了一束野花。还记得我说什么来着,他是个好人。话不多,腼腆,心善,像个大姑娘。我看他第一眼就知道了。
吃完饭,我和厨子到河边,他在河里洗洗涮涮,我继续编我的草席。我俩开始聊各自的打算。厨子说他想开个旅馆,外加面包店,他可以做点蛋糕饼干之类的卖。我也有我的打算,很多人在俄勒冈猎捕海狸,为的是把海狸皮毛卖到巴黎给贵妇们做帽子。可还有个财路他们都没看到,只有我看到了,就是海狸油,这东西可以做药,在中国能卖大价钱。可惜我在广州没人,如何运输也是个问题。这就是我这种穷人面对的问题,一无所有,如何起步?做生意需要资本,还需要点奇迹,也许还需要犯点罪。
晚上,我俩一边抽烟一边聊天,我跟厨子不知怎的特别聊得来。厨子说下午他在我打盹的时候又出去采野果,他看到了总领的那头牛。他说他吃厌了水加面粉做的饼,真想挤点牛奶做蛋糕。他的话忽然启发了我。这片泥沼之地上,想吃蛋糕的肯定不止他一个。我问他做蛋糕都需要什么原料?厨子说的那几样材料里面,除了牛奶,其他原料我都能搞到。我又问他,晚上能不能挤牛奶,会不会被人听到?厨子明白了我的意思,他摇了摇头。
我们还是去了。我爬上树替厨子望风,厨子开始挤奶,他可真有意思,一边挤奶一边跟奶牛唠家常,安慰奶牛来的路上死掉的家人,好像这牛真听得懂他的话似的。厨子是个靠谱的朋友,对牛都这么好,对人肯定也不会赖。
第二天早上,我在屋外洗漱完毕,然后去给我养的山鸡喂了点吃的,正要进屋时看到窗台上放着一个刚烤好的蛋糕,厨子站在一旁腼腆的笑。厨子的手艺真不错。我琢磨着这蛋糕如果拿到镇上去卖,得多少钱一个。厨子说他可不敢去卖,毕竟用了偷来的牛奶。我告诉他,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于是我俩去了镇广场。
我们只有6快蛋糕,转眼就卖完了,为了争最后一块蛋糕,那帮馋鬼宁愿加价。有些人问我们蛋糕是什么做的,我说那是个秘密,来自古老中国的秘密配方。感谢法国那帮启蒙文学家,在他们笔下,遥远的东方中国是一个无奇不有的秘境,西方人对我们充满仰慕,中国人可以创造奇迹。我有预感,我现在是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必能成事。
第一次销售很成功。我跟厨子说我们必须得继续,如果我们赚到一些钱,就可以去加州开他梦想中的旅店了。于是我俩的蛋糕生意正式运转起来了。
总领也听说了我们的蛋糕,他尝了之后赞不绝口,还说吃到了伦敦的味道。他想让厨子为他和一位即将来拜访的上校做一个法国蛋糕,我在旁边站立不安,厨子却应承了下来。回到家,我跟厨子说,我们必须得停手一阵子,那帮糙人吃蛋糕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可是总领的味觉很敏感,他不会吃不出来蛋糕里面加了牛奶。厨子慢悠悠的说,也许他不会往那想,有钱人就是很自信,想不到自己会被暗中欺侮。
厨子做的法国蛋糕让见过世面上校也不得不承认是那么回事。总领很满意。他们喝着中国红茶和法国蛋糕聊着海狸皮生意和巴黎的时尚风向。他们描述的世界离我太远了,这些人,自命不凡的上等人,连他们从法国运来的牛似乎都比我血统高贵。我和厨子回到家,厨子说上校可能看出来了他和那头牛有点猫腻。他不敢再去偷牛奶了。我跟他说我们不能停,像我们这样的人,只能靠自己,有机会就必须抓住。我们攒的钱还不够在旧金山立足,我们必须多赚一点,再多赚一点。命运的不公和对成功的渴望让我放弃了一贯的谨慎。
最后一次偷牛奶的时候,我们被发现了。我和厨子一路狂奔,后来我俩跑散了。隔天,我找到一个印第安人摆渡我回到下游,我必须回去我的小木屋,我和厨子的钱还藏在那里。等我靠近住处,我看到了厨子。谢天谢地,他还在,我俩的钱也在。厨子的头上有个伤口,我跟他说我们先离开这里,然后我在帮你处理伤口。我俩不知道走了有多远,厨子似乎再也走不动了,他径直在一棵树下躺倒,我看着即刻就睡过去的他,我想,那我也歇一会吧,我把钱袋子压在身下,在厨子身旁躺了下来。我俩,再也没有醒来。
我不怪那个杀了我们的少年。他为总领工作,更何况我们还带着那一袋子钱。如果我是他,保不齐我也会这么做。我说过,像我们这样什么都没有的人,有机会就一定要抓住。这世上,既有厨子这样的好人,也有绿衣少年那样的歹人。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办法努力活着。遇着什么,都是命。
我有遗憾吗?当然有!我想和厨子去旧金山开旅店,凭他的手艺和我的精明,我俩一定能干得不错。可是现在,各位看官你们也看到我们的结局了。不过话说回来,这样的命运,我也能平静的接受。当我在厨子身边躺下来的时候,最后一眼看了看这片天地,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最丰饶的美洲大陆,各种树木,花草,动物,都在我的身边,天空碧蓝澄净,微风吹过树梢,那一刻可真够美的。我两手空空踏上这片土地,吃的喝的用的全是这片土地给我的。这片土地从未辜负我。我能想象如果我活着,它还能给我什么。我拿了它的,会给它补回去个新的,我补回去的新玩意儿,它没准再加工处理变出来个它本来没有的。我能想象在这个无限的生机循环里,这片土地支撑着我,我也支撑着它,踏实。这就是我最后那一刻的感受,大地如此丰饶,它属于我,我属于它,日子有奔头,我心里很踏实。
很多年以后,俄勒冈这个地方出了个女导演,她把我和厨子的故事拍成了一部电影。有看了的人总结说这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的故事。我觉得这位观众说的有点意思。因为在我死前两年,德国特里尔有个孩子刚出生,他后来成了一位大思想家,我死后两个世纪的发生的大事小情都被他的思想所影响。他有一句名言也是他所有思想的起点: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我觉得按照这德国孩子的意思,这位观众好像是在骂我和厨子,我俩的故事不知怎的就成了他说的一个资本主义的故事,还流着血啊和什么肮脏的东西。其实我俩这事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厨子说他想吃蛋糕, 我从他的话里发现了商机,我看到了供需的存在,我和厨子有生产蛋糕的工具,我俩付出了劳动,我们合计出一块蛋糕的价格,我们在镇广场上完成了交易,销售收益让我们有盈余资金进行再生产。我和厨子对这一系列的生产和交换很满意,食客们也满意。我和厨子做的事情难道不是再自然不过的吗。我们确实有个无法否认的脏事就是牛奶是偷的,可这不是俄勒冈的第一头牛么,唯一的牛,唯一的牛奶,如果我当时大胆点,跟总领商量一下买他的牛奶或者用什么交换,如果总领是个精明的买卖人,而不是霸道的土皇帝,我和厨子也不会冒着被枪打死的风险去偷牛奶不是么。偷牛奶这事,我认,我俩不也是因为这事把命给搭进去了吗。可是其他什么血和肮脏的东西,我就不明白了。假如让那个德国孩子跟我一样两手空空来到俄勒冈,别带着那个给他提供了一辈子免费吃喝的小伙伴,他会怎么做? 反正,资本主义的事情我不懂,不过有好事者写了个东西把我和厨子的故事用资本主义的术语重新讲了一遍。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4 ) 第一头牛
在一段充满原始荒芜之地,两个怀揣梦想的人在这里相遇相识相知,在这片荒芜之地上的第一头牛,因为这头牛的牛奶足以改变两个人的命运,但正是因为牛奶让他们招来杀身之祸。是关于开拓者奋斗者的故事,却悄无声息的被资本抹杀在这荒芜之地上。那种无力感和凄凉,直击人心,最后的结尾和开头对照,这片荒芜之地是为他们梦想奋斗地方,他们也永远躺在在这一片荒芜之地上。这样一段故事却在导演的镜头中缓缓到来,精妙的构图和画面,细腻的感情融入在每一副画面当中。
5 ) 凯莉·雷查德的电影风格,《第一头牛》中真实生活空隙的延宕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陀螺电影(微信号:toroscope)
作者:鲜有废客
一个白人厨子,一个中国商人,相逢于1820年代的美国小镇,因为一头奶牛,两人发家创业,摆起地摊,售卖糕点;但也因为这次铤而走险的商机,令他们走向不归路。
影片《第一头牛》用一则少见的西部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华人在美国电影中的另一面——
既非满大人那样妖气横生,也不是华人劳工那种悲怆无声,而是用我们最熟悉的精明、不认命的形象出现。

《第一头牛》不仅仅是今年所有影迷都翘首以盼已久的电影,它也有很大希望角逐明年奥斯卡。
我们可以看到,烂番茄新鲜度96%,美国知名评分网站metacritic开分89分,可以说是万无一失的“年度必看电影”了。


年初的柏林电影节,陀螺在现场看完《第一头牛》时,也惊喜地打出了四星半的超级高分。

不过,这部在今年柏林电影节上亮相,入围主竞赛角逐金熊奖的影片,最令人瞩目的并非其华人题材,而在于它是一部凯莉·雷查德执导的新片。

一,新新现实主义?女性导演?
对于内地电影观众来说,凯莉·雷查德并不是一个熟悉的名字。
她既不像派蒂·杰金斯那样,因为《神奇女侠》的超高票房和影响力而为人熟知,也不像凯瑟琳·毕格罗那般,凭借《拆弹部队》跻身奥斯卡最佳导演之列。
但是从美国艺术电影和女性导演的作者性来看,凯莉·雷查德绝对不容忽视, 甚至有些影迷将其封为当代“香特尔·阿克曼”。

出生于1964年的凯莉·雷查德,从小对摄影产生兴趣,在从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附设学院获取硕士学位之后,她便开始参与拍摄独立电影。
1994年的《野草蔓生》是雷查德的长片处女作,凭借这部电影,她立即成为影坛新星,入围了圣丹斯电影节三项独立精神奖和评审团大奖。

单从类型题材来看,《野草蔓生》并不新鲜。
它将新好莱坞电影时期的《雌雄大盗》重新搬上银幕,让一个无所事事的街头混混,和一个生活了然无趣的家庭主妇组成亡命鸳鸯。

但影片越是发展到后面,越是呈现出一种荒诞和解构意味。
男女主角本以为枪杀了一名黑人而驾车逃亡,实际上,这名黑人毫发无损。 当逃亡失去了意义,伴随逃亡旅程而滋生的快意浪漫,自然显出虚无。

用美国底层家庭中的庸碌无趣,套上公路类型片,加上大量的摇滚乐、爵士乐,以及闪回、序号篇章画面—— 雷查德给这桩无疾而终的逃亡之旅,盖上了一个重重的黑色邮戳,寄往无数内心空洞的中年人面前。
该片在艺术上取得成功之后,雷查德本打算继续拍摄电影,然而由于女性身份的限制,令她在筹资拍摄的过程中常常陷入绝望。最终,只能用超八毫米摄影机拍摄短故事片和纪录片。
所以,在2006年拍摄《昨日欢愉》之前,雷查德一直处于理想和现实的撕裂—— 想要拍摄的题材与所筹集的资金之间无法缝合。在此期间,她潜心于教学,成为巴德学院电影和电子艺术的常驻艺术家。 幸而她和托德·海因斯(《天鹅绒金矿》《卡罗尔》导演)是多年老友,才让她的导演生涯出现转机。

不过,这种转机并非主要因为海因斯在经济上的门路, 而是他的一位文艺圈朋友——乔纳森·雷蒙德成了凯莉·雷查德直至今日的灵感来源。

当时,雷查德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故事拍成电影,雷蒙德刚好有一部剧情简单的小说。 两人在海因斯的牵线搭桥下,由此开始了不分彼此的长久合作。而这一小说便是《昨日欢愉》。

如果说《野草蔓生》让雷查德的电影才华为影坛共见,那么《昨日欢愉》则开创了雷查德以长镜头为主、绝少对话的朴素写实风格。
这部电影的故事异常简单,一个妻子怀有身孕的事业男马克,和另一个过着嬉皮士生活的邋遢男库尔特,两人相约到山上泡个温泉叙叙旧。

影片在两人静默开车和赏景,以及充满焦虑和怀旧的对话中,缓缓流淌。 雷查德对于布什政府的质疑,对于步入中年的美国底层男性的剖析,在此形成一条相互影响的螺旋体。
两年后,雷查德又将雷蒙德的短篇小说《火车合唱团》,改编为电影《温蒂和露茜》,获得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由此掀起了关于美国“新新现实主义”流派的讨论。

《纽约时报》的首席电影评论家A·O·斯考特,曾在2009年3月撰文提出了“新新现实主义”这一流派, 并将雷查德的《温蒂和露茜》作为代表提出。

在观看这部电影时,让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同类电影,除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流派,便是达内兄弟的《罗塞塔》。
同样都是青涩毛躁的小姑娘,同样都是急需工作的社会底层,不同的是—— 《罗塞塔》讲述的是阶级困境中人物的下滑挣扎, 而《温蒂和露茜》展现的是下层群体因贫穷导致的匮乏感和无力感。

2010年的《米克的近路》,雷查德用特殊的女性视角,将一直令美国骄傲的西部片神话彻底颠覆。
让一群淘金者,听从一个印第安人的指挥找寻求生的水源,西部拓荒的伟大精神,在此成为一则吊诡的政治寓言。

不少人将这则故事,解读为布什政府期间的伊拉克战争,
美国国民是那群淘金者,而有着种族偏见的引路人米克隐喻了总统布什。

2013年,讲述三名环保主义者为引起人们重视,炸毁大坝的《夜色行动》成为雷查德电影序列中口碑最差的一部。 虽然有杰西·艾森伯格的加持,但平淡无奇的剧情,以及缺乏信服力的人物行为逻辑,让整部电影流俗无趣。

好在2016年的《某种女人》重新回到熟悉的“凯莉·雷查德”风格。
虽然是三段式的女性小品,但每一个故事都在寻找女性日常生活中的坚韧和个性。这部影片刚下映没多久,就被著名蓝光碟产商CC收录发行。

这么多年来,仅这六部长片,就令关注电影艺术最新潮流的评论者们为凯莉·雷查德探讨不断,她到底是一位新新现实主义的开创人?还是执着强硬的女性导演作者?
或许问题的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雷查德的魅力,更多是一种站在左派立场,用女性视角重新审视现实和历史的丰盈和凝滞。
二,憨直的《第一头牛》
了解了雷查德这位女性导演的一路历程,再来欣赏这部《第一头牛》,我们便不只是会将视线聚焦于那位远渡重洋的中国人身上。
这部影片同样改编自雷查德的老伙伴乔纳森·雷蒙德的小说,而且是他在2004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半条命》,雷查德之所以当初没拍,在于这部小说的故事过于复杂,这对那时还处于资金短缺的她来说,自然难以驾驭。
即使是此次的《第一头牛》,也只是截取了原著小说中的一条线索而已。 在1820年的美国,俄勒冈州的一些小镇尚处于发展初期,印第安人、英国人和各国的淘金者群聚于此,都在为早期的财富积累冒险。

中国商人金路在机缘巧合下,被来自马里兰的厨子奥提斯救了一命。
为了报恩,金路邀请奥提斯和自己同住,一起寻找发财的机会。

没多久机会来了,小镇上的英国总领费克多花费重金,从欧洲买来一头优质奶牛,只为喝到纯真的奶茶。而这头奶牛,成为这块土地上,迄今为止的第一头牛。

恰好奥提斯感叹自己制作的面包,如果能加入牛奶,一定美味无比。

为了满足好友的愿望,金路大胆提出,两人一起夜间偷偷挤牛奶。
在尝到奥提斯制作的牛奶蛋糕口味不凡后,金路心中涌现出一条商机: 到集市上贩卖蛋糕。 果不其然,蛋糕不但瞬间售空,而且有人愿意抬价购买。 这让一直渴望发财的金路尝到了甜头。

就这样,金路站在树上放哨,奥提斯在下面挤牛奶,两人合作,财富日益增多。
直到总领费克多也不惜屈身,来到奥提斯的小摊前品尝时,危机开始了。 费克多虽然没尝出蛋糕里添加了牛奶,但是却看重了奥提斯的厨艺,盛赞之下,想邀请他制作更高级的法国糕点,到自己的宅邸为其在人前添光。

奥提斯作为底层小民,当然不敢抗命。可金路心有城府,知道偷牛奶的事情不久便会曝光。

在两人到总领家献上法国糕点之后,总领邀请他们一同观看那第一头牛。而这头牛奶也像宠物一样,对总领这位正经主人冷淡疏远,反倒对天天夜里给他做“胸部按摩”的奥提斯亲昵有加, 这让总领身边的军士深感怀疑。

当天夜里,在两人再次偷奶时,意外发生了。
金路放哨时,踩断树枝,惊动了总领家的侍从。奥提斯带着金路一路逃跑,顾不及倒翻的牛奶罐子。 总领看到有人偷牛奶,瞬间震怒。他知道,整个镇上只有两人可能偷奶,那就是金路和奥提斯。
在电影一开始,便展现了一个现代人在河岸挖出两具白骨的桥段。 所以,看到金路和奥提斯被总领追捕,我们自然以为,电影最后会呈现两人遇害的情节。

可一如雷查德之前的其他电影,本片以受伤的奥提斯和疲惫的金路躺在地上休息而结束,他们两人究竟是否被杀,我们不得而知。
很多人将这部电影,看作美国资本主义早期财富积累的历史片,然而导演雷查德显然既不是一个历史爱好者,也非正襟危坐的政治批判者。
确实,不管是英国总领耗费巨资引入奶牛,还是普通平民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现状,都让本片带有浓重的批评立场。 但英国总领的“朱门酒肉臭”更多是以滑稽的丑态来亮相,而非残酷的病态来曝光。

《第一头牛》的光影魅力,在于它对真实生活空隙的延宕,对于憨态人物的沉迷,对于油画质感的涂抹,以及对财富匮乏的感叹。
在金路和奥提斯在小镇上再次相逢后,金路热情地邀请这位救命恩人到家中做客。一路上,金路和奥提斯随意攀谈,到家中后,也如同许久未见的老友敬酒寒暄。 两人说到停歇处,并没有一丝尴尬,反而有着底层人家闲扯后的遐思,或者叹息处的呆滞。

显然,这是从《昨日欢愉》中延续而来的真实生活空隙。
雷查德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两个男性之间的对话,她用女性敏感的情思,咂摸出男性对谈中必然的落空。 这种落空包含真诚,因为真诚注定不属于话痨絮语,而归于情感抽空的暂时延宕。 沿着这种场景中的延宕,我们便能感受到片中太多人物的憨态。

最明显的就是厨子奥提斯,他是一个买了新鞋,在引人注意之后都会扯下裤脚遮掩高靴的憨人。
憨到在为奶牛挤奶时,对它感谢不已;
憨到这辈子只想开个面包店,好好做个厨子;
憨到别人出去打架,让他帮忙看孩子,他也安分答应。

但憨人往往有赤心。奥提斯会为了牛奶失去“丈夫”和“孩子”而动容,也会因为看到素昧谋面的可怜中国人,为他担着干系,救他一命。
以至于,夸奥提斯靴子的老人。

带孩子到酒吧的肥胖父亲。

都憨态可掬,底层味十足。
在《昨日欢愉》中的嬉皮士库尔特,或者《某种女人》中的牧马女,都有这一憨性基因。

这不禁让人想到梵高早期的素描画。当他在荷兰朝着那些挖土豆、做农活的农夫农妇写生素描时, 荷兰农民的憨直木讷,在梵高憨勉愣头的笔触下,足以让人感动。

感动的不是憨性中的笨,而是憨态中的真。
在我看来,雷查德虽然在处女作《野草蔓生》中才情肆意,知道在哪处添段闪回,在哪处插入摇滚乐, 生猛灵动的劲儿,不下于丹尼·博伊尔在《猜火车》中对于声画的天才处理。
因此,完全可以将雷查德归为聪明灵巧的导演。然而,她在电影中却喜欢刻画笨人物,也喜欢下笨功夫。 这种“笨”,也能在梵高的风景油画中找到对应。换句话来说,这是一种滞重粘稠的触感。

在《温蒂和露茜》中, 让温蒂一次又一次拨打老警卫的手机,或者穿梭于人来人往的街道。

在《某种女人》中,让牧马女重复性地喂马草料, 或者在女律师的城市来回寻找。

没有配乐,没有戏剧冲突,而是用积累下来的焦虑、等待情绪重复性地出现在画面中。
这和同样以现实主义闻名的格斯·范·桑特不同,他要疏远和形式化得多; 也和英国的肯·洛奇和伊朗的阿斯哈·法哈蒂不同,这两个人有着张力十足的叙事冲突。
雷查德完全不在乎重复带来的臃肿,因为如同梵高的油画一样,看似粗犷而漫不经心的重复线条,形成的却是对于生活真实的内部描摹。

《第一头牛》中的滞重感,是未开发的幽密丛林,是泥淖污浊的集市地面,也是贫穷造成的平民衣着。
当贫穷成为常态,匮乏感便掩盖不住。
这种匮乏感,在雷查德上一部电影《某种女人》中最明显。
片中的四个女人像雷查德自己诠释的:她们都在寻找着什么。 劳拉·邓恩寻找爱情和事业;米歇尔·威廉姆斯寻找家庭和亲情;莉莉·格斯莱顿寻找归属和温暖;克里斯汀·斯图尔特寻找稳定和认同。

但是在《第一头牛》中,由财富引发的匮乏感,让下层的生命像是变成匍匐前进的蜗牛, 总在近乎停滞的前进中寻找方向感,以及迫切想知道找准方向之后何时才能到达。

对于这个残酷的问题,雷查德选择了一如既往的回答方式:让两个人就地躺在丛林中。 枪手是否会射死他们?现代人翻出的两具白骨是不是他们?他们是否实现梦想,一个开了旅店,一个开了面包店? 一切都付诸于继续无常且无尽的真实生活中。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陀螺电影(微信号:toroscope)
作者:鲜有废客
6 ) 第一頭牛(First Cow,2019)
1、片頭威廉布雷克的箴言「The bird a nest, the spider a web, man friendship.」是第一頭牛(First Cow,2019)這部電影開宗明義的宗旨所在——情誼,或者用中國思想的語言來說,就是朋友倫。
2、原始人類為了生存發展,很快的就進入了以合作為內涵的社會運作中,因此,人除了是個體之外,還是群體的動物,是社會者人——故事集中在論語所謂「有朋自遠方來」的這個層次。
3、第一頭牛這部電影涉及了兩個人際關係的層次,一是朋友倫,二是君臣倫,由於電影中的兩個主角是光棍,並且隻身離鄉,所以可以說是沒有夫妻倫、父子倫、兄弟倫關係的描寫與基礎。在朋友倫和君臣倫(君者群也,指個人與組織、社會或國家的關係)的故事設計中,又以賤君臣的方式凸顯友誼之貴——他們雖偷盜牛奶,破壞社會的秩序性,可是卻無損於觀眾對他們的愛好和同情,因為盜亦有道,況且這小小的偷盜是起源於資源不足並且分配不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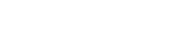




















4.5 不断想起《花村》和《希斯特斯兄弟》,但雷查德毕竟是雷查德,西部片里鲜有的男性形象,最终还是被她发现了。这是一个暴力肮脏的世界,但也有轻柔的细语,也有田园的陪伴。在雷查德的世界里,周遭的环境终于不再死气沉沉,似乎被注入了一些灵魂。
4.5 这荒蛮之中的温柔太动人,就连最后那一点不可避免的残酷也化作了浪漫的永恒。
为什么说雷查德的电影是一种新的电影?因为站在前人白骨之上来反思我们当下世界的她,看待历史的眼界有了变化。一种纤细敏感的女性视角发现了一段伟大友谊和一个理想境界曾经存在的证据,影片为我们这些挣扎在资本主义时代的人考古出了一份关于资本原则必然死亡的证明,以及它的尸检报告。所谓《第一头牛》既是两个现代资本家的第一桶金,也是两个无产者最后守护的对象。他们是「NewMoney」的接生婆,同时也是被「OldMoney」驱逐的乞丐。牛奶越挤越少,面包也越来越没有了家的味道。像大自然里一切濒临灭绝的事物一样,这头母牛死于无法传承和延续。两个男人为了食物和财富凑到一起,最终被这片富饶的土地埋葬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从绝望到希望,雷查德的镜头衔接得如此美妙,整个过程在她营造的自然主义美学氛围里宛如一首绵长的叙事诗。
自然影像的新鲜生命力不逊于两位主角,或者说,当河流上的独木舟变作货轮,二人间的友情历经沧海桑田,亦化作了静谧而深邃的环境的一部分,雷查德将影像变作草木,深深扎根于主流叙事的边角,等候朴实诚恳的灵魂前来发现、欣赏。
#70th Berlinale#主竞赛国际首映。特柳赖德电影节首映。聚焦1820年代俄勒冈地区,白人“Cookie”和华人“King-Lu”之间的兄弟情谊,影片至多能算是“西部题材”,写西部的日常生活,两位“死得同穴”的准基友实在是讨喜(不过华人这个角色英语是太流利和没口音了点),有不少相当有趣的细节引人发笑。慢慢悠悠之外,视听风格还体现在常见的提喻修辞(部分代整体),还颇用了一些转移注意力的景深镜头调度技巧(门框窗框的使用等)。美服化道下了大工夫,摄影使用4:3画幅,相应地也更多地把焦点放在人物而不是风景上。华裔担任双男主之一的西部题材恐怕是相当少见。
那晚我梦见,在果冻一样的河里,和小猫击掌分享小鱼干
4.5;仿佛是《昨日欢愉》的另类变奏与延宕回声,再次被凯莉·雷查德式的自然主义所打动。在被“封闭”的树林空间内始终有望向外部的目光(对应门窗框分割出的构图与视线),始终有资本力量的流入而影响改变着人物的命运,「第一头牛」成为窥见拓荒期经济结构和人员分布的支点——从两位男主具有商业意识的先期“开发”,到最终会被“主人”配对、被豢养。残酷西进历程以萍水相逢的惺惺相惜来呈现微末历史一角,不无温暖和幽默,荡漾着细碎的、浅浅的温柔,像踏过落叶地的窸窣,像火苗卷过树枝的哔啵,像水流曼过船桨的欸乃(日常拍得太好看了!),他们在广阔天地相逢并不曾互弃,在贪婪蛮荒之地寻求到互依,他们以血肉之驱与大地拥抱,呼应开头真是百感交集。
自然主义。简单的纯粹故事。弱化时空的历史性社会性。非常自然的表演。这类纯粹的元故事很仰仗导演的视觉化,就这个层面来讲做得是非常好的。
生同袍,死同穴,拓荒汉的柔情我们永远不懂。接近方形的复古镜头,牛挤出来的是乳汁也是人性温柔。这世道越来越魔幻了,中美两国人民只有在文艺片里才能不掰头...
雷查德总能将野性与温柔恰到好处地融合,这部新作在静缓之中隐伏着张力,简约小格局的文本与场景之中,蕴含着丰富而真实的影像密度。那些细腻的自然环境音与用心的服化道,足以令人沉入旧时西部。影片全然关注着个人,注视着两位异族移民间的挚朴友情与他们略显寒酸的野心,这是一次对小人物跌宕命运的深情凝望,展露出以往隐没于美国梦宏大叙事背后的残酷底质。传统学院派的画幅比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观者的视角,西部广袤壮阔的全景在影片中也基本缺席,时代背景与人物前史仅由只言片语提及,于是,重心便转移到了个体的生存斗争与互助情谊之中。男主被救后躺在木屋里醒来时的主观镜头被模糊了边缘,恍若命运投(头)下的阴霾。戛然而止的收尾联系片头后显得如此怅然,他们至终没能用上第一桶金,没能去往那片奶与蜜之地。(9.0/10)
仿佛串起了Kelly电影“宇宙”下的前世今生:《旧梦》已过十三年,穿梭于绿意间的老友们又重新回到了两百多年前,走上另一条路;Alia Shawkat开头的造型,出镜的Lily Gladstone,梦回《某种女人》;作为戏多的观众,很乐意享受这种自己因为发现点小线索而陷入的所谓“沾沾自喜”。最诚意的乐趣依然在于它对自然最温柔的注视和一种近似于肖像临摹般的生活描写,行之所踪,都充满着最简单的生动和不加附注的聚焦。会很沉浸于这两小时所上路的“启程”所发生的种种,以及犹如老友陪伴的直接,那就是最开始愿意关注和喜欢她作品的原因。
让人疑惑的电影。雷查德?还是雷查德贴牌的圣丹斯random guy?
猎人争相追逐的海狸毛皮,早已是巴黎退潮的时尚。穷人赖以为生的奶牛乳汁,不过是贵族红茶的点缀。窃取土地的殖民者追捕偷奶的窃贼,失却文明的原住民好奇远处的文明。海狸数量锐减,奶牛即将成群,历史洪流到来之前,糕点的秘方被埋入地下。气味被奶牛记得,白骨被家犬寻得,只剩后世猜测他们的秘闻。
What is this 浪漫爱情电影??两个小时片长像二十分钟一般过去,并不是因为情节紧节奏快而感到时光飞逝,反倒是由于疏松沉静,如在林中徜徉,方向和标点似有若无——第一次瞄见进度条时影片已进行了四十分钟,我却以为连十分钟都不到。开头William Blake的引用,“The bird a nest, the spider a web, man friendship.”本片是以情为锚,筑了一个温暖的巢,又抖开一张无形的巨网;在世上生存漂泊的旅人、在帝国与蛮荒间流动堆积的资本、赤裸的与穿衣的、土生的与外来的,都被那一点甜香系在一起。黄金是一场梦,而永恒的在无需商议地一同砍柴、扫地、洗衣、做饭里。牛被圈起,人已比翼飞。想看更多腼腆白男被魅力亚裔 sweep him off his feet(x
一部温柔的反西部片,暂时今年新片最爱了。凯莉·莱卡特实越来越娴熟了,故事不紧不慢,有浪漫也有伤感。剧情本身并不是特别复杂,却因为她一贯的写实处理方式,而更增加了些生活的味道,如回到那个年代。看外媒也不断cue《花村》,在视觉风格上,确实有些许相似。一个即残酷又温柔的故事,尤其那个结尾,很有余味。真的是很舒服的一部电影,也是今年比较少见的佳作。
家里安装了个海信84寸大电视,看片室有如小影院;于是开始了每日一片的观影。本片是《时代》杂志推荐的2020十佳电影的第一名,慕名找来观看。 又是一名女导演的作品,简洁而朴素地再现了二百年前美国西部开发时代的历史情境。写了一个华人淘金者与白人厨师的友情,这倒是我第一次在美国片里,看到了一位这么正面、智慧、善良的华人形象,值得夸奖。 导演采用了4:3的老式画幅,叙事节制,情节却起伏引人。片头的引文“鸟有巢,蜘蛛有网,人有友谊。”,概括了主题。 耐得下心的观众,可以琢磨出影片的许多好处。
博尔赫斯说过,“它不受时间限制,不可计数,等于零,它是最后也是第一头野牛。”
整部电影就像主角Cookie一样,腼腆、温柔,藏着不为人知的可贵才华,却毫无野心地只是轻轻地和观众诉说一段往事。人和人之间的友谊有个很难拿捏的度,雷查德的片却总是做得那么恰到好处,实在是太厉害了。“旧梦”重温!
A / 凯莉·雷查德构建“生态”的能力几乎超越了之前所有的作品。与其说她呈现的是一段单纯的友谊,不如说她更在意的是这种情感如何被嵌入了一段如花苞般尚未舒展开的历史时空中——就像片名一样,一个被悬置的开端。由此她的4:3画幅聚焦的便不只是两个主角,还有擦肩而过的人艳羡靴子的呢喃、蹒跚的印第安女孩的步伐、老人的木头小屋与门前的尘埃,更有森林中野兽的目光……如此种种都在这片尚未接入现代文明的界域创造了一个更内在的世界。在这一茂盛的力场中,影片的情感时间开启于砍柴与抖落地毯灰尘交织的二重奏,终结于两种呼吸的永恒。而穿越时空之后,那艘伫立着一头牛向我们漂游而来的船变成了嗡鸣的巨轮,这荒凉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人美心善的厨子小哥遇上向往田园的圈钱奇才,偷奶做饼是合作无间,流离失散仍情比金坚,可惜梦碎魂销一场空,徒留白骨成双叹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