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长篇影评
1 ) Eine grausig wahrheitsgetreue Darstellung
Der Goldene Handschuh ist ein deutsch-französischer Spielfilm von Regisseur Fatih Akin aus dem Jahr 2019. Der Film erzählt die Horrorgeschichte des Frauenmörders Fritz Honka aus dem Hamburger Kiezmilieu der 1970er Jahre und basiert auf dem gleichnamigen Roman von Heinz Strunk. Er hatte auf der Berlinale 2019 seine Premiere und wurde im Hauptwettbewerb gezeigt. Der Goldene Handschuh ist nach der Kneipe im Rotlichtviertel in Hamburg benannt, wo Honka seine Opfer traf.
St. Pauli in Hamburg in den 1970er Jahren ist eine Nachbarschaft von nächtlicher Unterhaltung und ihrer nachtaktiven Persönlichkeiten: Gewohnheitstrinker*innen und Sexarbeiter*innen, Glücksspielsüchtige und andere einsame Seelen. Fritz Honka, ein kleiner Mann mit einer dicken Hornbrille und einem unvorteilhaften Gesicht, ist einer von ihnen. Als ungelernter Arbeiter greift er in einem Stammlokal namens Zum Goldenen Handschuh einsame, ältere, sozial verwahrloste Frauen auf. Niemand merkt, dass er diese Frauen in seiner Dachgeschosswohnung schlägt und erwürgt, sie dann zerstückelt und ihre sterblichen Überreste hinter der Dachbodenmauer entsorgt. Er verteilt duftende Lufterfrischer in der ganzen Wohnung, vor allem neben den verrottenden Körperteilen, um den Gestank der sich zersetzenden Leichen zu verschleiern, und gibt der benachbarten griechischen Familie die Schuld an den durchdringenden Gerüchen.
Basierend auf dem echten Fall des Serienmörders Fritz Honka und dem Kriminalroman von Heinz Strunk aus dem Jahr 2016 hat Fatih Akin ein Porträt eines sozial verdorbenen, gewalttätigen Verbrechers geschaffen, der von Frauenfeindlichkeit, sexueller Gier und Wahnvorstellungen getrieben wird. Akins Film ist eine soziale Studie über die Kehrseite des jüngsten Wirtschaftswunders: es geht um Menschen, die durch den Krieg und die Nachkriegsunruhen in einem dunklen, an Selbstvertrauen mangelnden Deutschland aus dem Gleichgewicht geraten sind.
Obwohl fesselnd in Hinsicht auf einen Einblick in einen kriminellen Geist, ist Der Goldene Handschuh übermäßig blutrünstig und grauenvoll. Der 110-minütige Film begibt sich auf einen gut gemachten, aber zutiefst unappetitlichen Abstieg in den verdorbenen Verstand und die grobe Brutalität eines Serienmörders. Die originalgetreue Ausstattung schafft es vor allem die unbeschreiblich elenden Zustände, in denen Honka lebt, authentisch zu porträtieren, und die drastische Darstellung von Gewalt gegen Frauen und das Entsorgen der Leichen ist nicht weniger real dargestellt, aber die Details sind allzu widerlich. Die ekelhaft detaillierte Schilderung des Zerschneidens von Körpern erinnert an Lars von Triers Film 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 Doch das ist nicht als Kompliment gemeint. Ob Magen umdrehende, blutige Bilder wirklich absolut notwendig sind um eine Mordgeschichte zu erzählen, steht zur Debatte.
2 ) 真是被折服了
阿金不用多介绍了,93年的男主、一群大妈们的演技也是好的一B,绝对入戏。翻了翻影评,大多是恶心、负面、反其道而行之、有失水准之类的... ...
我能说我看了以后直呼过瘾吗?画面真实,代入感极强,服装、道具、场景更是高度还原,仿佛置身70年代颓废的西德,也感受到了当时人们谈洪卡色变的震慑力。
总之,可以断定阿金拼了,不顾一切想超越这部小说所能带给读者和观众的一切!

3 ) 牛逼(请配上昆汀的那个表情)
整片看下来就是一堆腐烂的肉在慢慢变臭的过程,如果现实是这样,那无论下地狱或是上天堂都至少是个结果。
演员牺牲很大,这个工作完成了不得出戏几个月啊。战争如果过了打鸡血的过程,很容易让牵连者沉入烂泥里。
最棒的安排就是那场大火阻止了洪卡染指那位天使,导演你还是给世俗留下一丝光亮的。
4 ) 可恨人必有可怜之处。
真的,有时候感觉男主也很悲哀,一路走来,这些女人都是在欺骗男主。第一个,是知道男主好女色,就骗他有个女儿,好让男主养着她。同样的第二个女的是那3个女人中的一个,说好的请他们喝酒他们就跟男主回家,这本来就是一种下意识的交易了。一个醉酒不起,一个骗男主趁机跑了,最后一个那种情况还想趁机多喝男主的酒,也就没有好下场了。第三个,虽然作做很高雅的样子,确实下手最低劣,本来就在那种情况还嘲笑男主,羞耻于男主,事后还用黄芥末,抹男主。我的天这跟把男主杀了有什么区别。第4个还是同样的,喝酒,到了最后一步还想用这种化学阉割的手法来保护自己?怎么?谈好的一瓶酒,最后还想敲竹杠?哦,还有一个,女厕清洁工,不过男主没有得手,也很有意思,丈夫不去工作没钱,就来勾引男主,让男主爱上她,重新诱使他喝酒,想让男主做备胎没钱了就找他来拿。但是男主爱的是她,她却想介绍自己的姐姐给男主认识,这样,男主仿佛就永远是她的ATM了。
5 ) 这部重口味经典,不止有限制级的场面,提名金熊奖的它撕开了现实
移民德国的土耳其后裔法提赫·阿金今年持“恶”行凶,送上了超重口味的犯罪片《金手套》。

该片背景放在了70年代的德国,讲述了一个名叫弗里茨·洪卡的心理变态罪犯在德国汉堡红灯区接连谋杀了四名女子的恐怖行径。影片以他挑选“猎物”的酒吧,“金手套”作为片名。
2017年,具有移民背景的法提赫·阿金执导了由黛安·克鲁格主演的《凭空而来》,通过一位母亲的视角,讲述了当代德国人在新纳粹主义下的德国寻求公平和正义的故事。

该片获得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提名金棕榈奖,并帮助女主角黛安·克鲁格拿下戛纳影后桂冠。两年之后,法提赫·阿金的这部《金手套》尺度直逼去年的超重口神作,拉斯·冯·提尔的《此房是我造》。

如果说《此房是我造》是精神美学的巅峰,那么《金手套》就是现实主义的一记闷锤!

首先吗,影片故事并非虚构,而是取材真实事件;另外,通过极度风格化的影像建构,银幕以舞台室内剧的方式,逼真“再现”了当时的恐怖场景。
法提赫·阿金罕见的在《金手套》里消解了戏剧性,空间感,力求让拟态化的电影叙事与真实过往不断重叠。

对于真实性的强调,很清晰的由他的场面调度、镜头语言与空间设计表现出来。影片一开场就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杀戮场面,没有交代前因,直接就呈现出洪卡第一次犯案的残暴行径。这一场戏与《此房是我造》有相互致敬之处,洪卡也表现出连环杀人犯杰克在第一次行凶时的慌张和不知所措,中途的精神崩溃,以及最后的极端冷漠。

法提赫·阿金在表现这段具有极强视觉冲击力的内容时,却配以最为简单“机械”镜头调度。没有明显的剪辑痕迹,在封闭狭小的室内空间里,配以“凝固”似的长镜头,逼迫观众目睹这场令人生理不适的惊悚场面。
镜头坚定的实践了安德烈·巴赞的影像本体论法则,实现了“影像与被摄物同一”的表现手法,让影片成为向世界敞开的一扇窗户。通过这扇窗户,观众窥探到了当年不为人知的犯罪现场的“真实”一幕。法提赫·阿金的用意非常明显,开场就让观众反感和不适,让观众对暴力和血腥场景逐渐“脱敏”,以便其透过暴力,一探人性深处的幽暗,以及压抑人性的历史大环境。
法提赫·阿金在影片里始终限制着蒙太奇的发挥,那些惊悚的血腥场面,混合了现实与虚构的叙事内容,在银幕上具有了真实的空间密度。

不做美化,只求真实。影片绝大多数时间里摄像机仅小幅度运动,以此让观众和男主角洪卡的主观视线同构。摄像机的微妙运动仅用来表现洪卡精神世界对外部环境的条件反映。长时间的高度的重合,让观众与罪犯的心理发生了奇妙的投射作用,观众随着镜头,跟着洪卡的视线转移,将焦点对准到新的“猎物”身上。

《金手套》有大量的室内戏,一个是洪卡生活的顶层小阁楼,杀戮和藏尸之地;一个是他与外界联系、搜寻猎物的地方——金手套酒吧;还有一个是影片后半段,他新的工作场所,封闭的办公室和休息间。
在室内调度上,法提赫·阿金借鉴了德国导演法斯宾德的《恐惧吞噬灵魂》。比如在室内酒吧的吧台上以斜对角式构图为主调,再配以多角度的正反打,营造出人物之间的疏离感,以及重要人物的视觉压迫感。

在阁楼内和楼梯上同样选用仰俯镜头对打与障碍物体遮挡切割构图边缘的方法,利用高度差、画面分割,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凸显冷漠与疏离。

而在阁楼房间内,法提赫·阿金多基本放弃了正反打,采用中景双人镜头,表现人物的暴力、人与人之间突然的沉默,在喃喃自语中捕捉流动的窒息感与爱无可诉。法提赫·阿金在《金手套》里,一反常规类型片,用摄影机镜头摆脱了我们对客体的习惯性看法和偏见,清除了我们感觉蒙在客体上的精神锈斑,因为唯有这种“冷眼旁观”的镜头才能还世界和人物以真实的原貌。
所以,《金手套》里的重口味血腥场景不过是为了营造一种真实,以此刺激观众的神经,消除麻木,吸引注意力,让理性复苏,以便成功传递他想通过影片传达的主观思想。法提赫·阿金“打开”了变态杀人犯洪卡的内心世界,让观众透过他与外界的交流,透视了一个时代的悲剧。

法提赫·阿金不光在镜头上借鉴了法斯宾德,他同法斯宾德一样,坚信“电影解放心智”,竭力伸出批判矛头,用电影倾吐自己内心的思绪。《金手套》执着于以一种历史的厚重来审判德意志民族沉重的罪孽意识。

影片把年代放置在德国70年代,用意颇深。虽然没有直接表现时代的疮痍,但通过男主角洪卡,以及围绕洪卡而展开的诸多二级人物,就可窥见人在时代中的异化。影片中的洪卡并非完全陷入癫狂的杀人犯,他在暴躁失控与自卑压抑中挣扎、焦虑着。

表面上看,影片叙述的是洪卡的杀人经历,但潜文本其实用洪卡的特性隐喻70年代的联邦德国。

当时的西德看似已经济腾飞,但因为铁幕的存在,以及柏林墙的分隔,让很多德国人依然感受到强烈的挫败感。洪卡的自卑和病态代表着70年代西德人的整体情景,个人的焦虑被社会放大。在虚假繁荣、政治附庸的情况下,部分西德人被绝望笼罩、陷入颓废,个体贫瘠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让他们不分昼夜聚集在类似“金手套”这样的酒吧中,利用酒精自我麻痹。

围绕洪卡的那些二级人物,包括洪卡杀害的女人大都来自这个酒吧中。他们看似活着,但早已失去了灵魂,只剩下衰老的身躯,退化的大脑,以及对酒精上瘾的绝症。
在“金手套”酒吧里出现的人物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符号,听力和视力都受损的老党卫军、曾经在集中营里生活过的妓女、失业的流浪汉,无所事事的颓废老女人。他们有的面对萧条的战后社会,反而愈发怀念战争年代的“荣光”。他们将一切归咎于战争的失败,暴力与渴望复仇的念想在心中积蓄;

他们有的开始自暴自弃,用酒精麻醉自己,仇视一切,甚至怨恨上帝。更可怕的是,社会的腐化不仅仅在酒吧中滋生,在酒吧之外的学校里也悄然发生着。

洪卡一直迷恋的女学生,开始被老师教导“一定要学习才有未来”,可她依然我行我素,靠着青春无视一切。最后,她在年轻男学生的诱导下,来到了“金手套”酒吧,再次激起了洪卡的欲望。

片尾,她虽然逃过了重新陷入疯狂的洪卡的摧残,但她没有想到过,危险曾离她如此之近,杀手尾随她走过了几条街。

她逃过了洪卡,但在那样的时代中,某个阴暗的角落里,也许还有另一个“洪卡”在等着她。

而她未来也极有可能成为“金手套”酒吧里,那些吹嘘自己年轻时美貌逼人,现在却衰老丑陋的女酒鬼。

影片里的两位年轻男女,在上一代的“教导”下,极有可能以镜子式的存在,陷入命运的循环,一直腐烂下去,一代又一代。

再看看片中象征着德国中产的中年夫妻,一个为了生活在洪卡所在的公司当清洁工,而她的丈夫刚刚失业,两人都陷入低谷,借酒消愁。更可怕的是,女清洁工还将洪卡重新拉回了地狱,令他变回了恶魔。

这是影片最明显的点题处。喝醉被撞伤的洪卡原本打算戒掉酒精。虽然经过了痛苦的戒断过程,但他明显好转,找到了新的工作,而且和旁人有了良好的人际交往。可一切都在女清洁工递出的那杯酒后急转直下。

洪卡重回酒精怀抱,宣泄情欲和暴力的杀人恶魔重回人间。

所以,是当时的社会情境造就了洪卡,深陷其中的洪卡想要逃离,却倍感无力。在法提赫·阿金的影像世界里,他人即地狱,爱比死更冷,人人都是一座孤岛,要么在酒精里昏昏度日,要么以死亡终结一切。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在《金手套》里,法提赫·阿金继续表现了移民文化给德国带来问题。

令人吊诡的是,影片中,居住在阁楼上的洪卡才是社会底层,而他楼下的希腊人位居中产。那种隐秘的寄生关系在一栋小楼里悄然发生。平时两个阶层的人相互之间不闻不问,因为工作和生活习惯问题相互咒骂、排斥。
可当洪卡藏着的尸体开始腐烂,生出蛆虫,而且从地板缝里,从上往下掉入希腊人精致的晚餐上时,两个阶层的人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恐怖的交集。

这种“共存”和“冲突”,显然比近来大热的韩国影片《寄生虫》来得更加生猛。《金手套》以冷峻、恐怖、逼真的方式,实现了电影的教化功能。正因为导演勇于表现丑恶,才使得电影本身成为了高尚最后的避难之所。
6 ) 拉片笔记
影片实际上并不“恐怖”。而且自始始终,就像德勒兹提到过的,影片有种魔力,能使所有不堪入目的东西都变得容易接受。那么我想,如果影像技巧是纯粹为了唤起感官刺激而恐怖,这就像去完成某种不可能的任务,注定会失败。导演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利用这种“不可能性”。 比如本片里,法提赫·阿金的做法值得引入经验。
联觉式转嫁(抽离)
首先是通过技巧,导演使不堪入目的影像“变质”了,转嫁给了“美妙的东西”,比如音乐和酒精。影片开始的第一场截肢场景中,杀手为了让自己舒缓情绪,喝了酒,同时可能是为了让观众舒缓情绪,打开了唱片机,舒缓优美的音乐随之而出,导演通过技巧强调了歌词:
刺激画面与美妙音乐的异质并置,导致了影像道德界限(暴力感/恶心感)的取消。刺激画面便容易被接受了,这是布朗肖(《死刑判决》)的伟大提示——“陌异感”能够取消界限。 随即,在杀手拿“酒”做诱饵引诱第一个活人到家里时,拿出酒杯的同时又打开了唱片机,同一首歌再次出现。这时,优美的旋律开始“变质”了,音乐携带了截肢的画面经验在观众记忆中唤醒,这首歌连带影片整体情境都变得“恐怖”了。优美与恐怖形成反差,相互勾芡。也就是恐怖感受是通过转嫁为听觉来体现的,而非纯粹的画面刺激。
这类对“联觉”的嫁接运用在电影里很多,比如上文提到的老太太最后虽然受到的身体性的虐待,但是至少是活着离开了,于是“听觉”的危机感被滞缓了,可一种新的感官嫁接模式也随即生成:嗅觉(炖-肉味);再比如杀手戒酒阶段对“红色”(女同事)的运用等。
质地转移
其次导演安排了角色视线“出画”。角色视线出画在影片中有两种功能,第一种是如介绍酒吧常客的戏剧式“亮相”,这是呈现给观众的,观众被设置成与影像对立的客体。这虽然是源自德国的戏剧传统,但这并非是纯粹的“布莱希特式间离效果”,“戏剧间离效果”是要让演员在角色和演员之间游离,演员有回归演员本身并面对观众的可能性。而在影片里,虽然酒吧里角色面对观众自我介绍了,介绍的却是“角色本身”。也就是说,也许是由于酒精导致的迷乱氛围的加持(非理性因素主导情境),这种“反身”反而是让角色更加可信了。

另一种是把观众强行置入角色行为与角色(变态)期待的中介位置——角色的幻想因观众的传递而成立,罪恶感因观众的传递而形成。观众因此被拖入“道德罪”之帮凶的行列。比如上图所示场景,在镜头A中杀手因为老妇人的话语和酒精作用,起了龌蹉的想法,便抬头面向观众邪笑,这时候杀手的视线“出画”了,与观众的视线交接了。紧接着蒙太奇镜头切入杀手的幻像:一个衣着性感的丰满女生在切肉(契合老妇人的话语的同时,也契合杀手的嗜好——切人,转喻用法;后来楼下“剪舌头”也是同样用法),随着镜头B的上摇,幻像中女生挑逗式神情回馈给杀手的同时,也强迫给了观众。而在杀手和性感少女的双重视觉胁迫下,观众被迫被夹在(正反打)中间,义务性的承担了视觉传递工作。于是,观众参与到了杀手的邪念之中,成了同谋。至此,观众不仅陷入了影片幻觉,同时也变成了影片内质的一部分——导演的险恶用心。
总结一下,也就是说,在影片的整体架构中,观众首先是被影像技巧从暴力画面道德感中抽身,然后又被强行置入另一个道德质问之中,观众因此开始面对真正的东西:审视自身的处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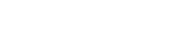




















#69th Berlinale# 主竞赛。阿金这次拼了,影评圈众口一词的关键词是“丑陋/Ugly”,阿金把这个连环杀手塑造得极为油腻猥琐,花了很大功夫去复原(令人作呕的)真实场景(因为就在导演年少时居住的街区附近,有个场景在导演的家庭纪录片里还出现过……)和展示施暴与虐杀,乃至分尸的场面,男主角表演确实很拼,影帝的有力争夺者。在剧作上倒是很用心,除了酗酒和性无能,还通过对金手套酒吧的场景复原和各色人物的描绘,谈到了二战创伤、移民问题,但更多的是年老和孤独。酒吧场景,以及男主角对肥胖老女人们的控制-虐待的很多场面,分分钟都让人想起法斯宾德。不过影片不只有邪恶和令人作呕,其间又幽默和纯真,有过卑微的善良,有过被救赎的希望但又更深地沉沦,这才是高级的情节剧。
【5.0】第一次看阿金,选了这么一片子感觉有点伤兴趣,制作实属不错,演员演得也是上乘,影像上也感觉很丰富成熟,但是总觉得看完少了点什么,就这?
哈萨克欧亚节主竞赛片,2001年我去柏林节做评委时该片导演法提赫阿金也是评委,当时他还是个刚出现的德国新秀导演,记得他对我国王小帅的参赛片《十七岁的单车》赞不绝口,不用我多说,在他的鼓动下我们给了该片评委会大奖。现在阿金已经是德国的重要导演了,可本片的血腥重口味还是吓着了我和许多同行们!根据七十年代的连续杀害四名老女人的变态杀人犯的真人事件,制作、演员很出色,但太恶心、黑暗,让人难以接受。
特别喜欢看法提赫·阿金导演的片子,非常的享受,他的片子在视听上总是那么精准,质量总是那么稳定,他最近几部作品风格各异,但什么题材都可以驾驭,水平在艺术片导演里算是顶级的行活水准了,视听永远都不会出错,剧作也不会有好莱坞模式化的展开。这部新片在用犯罪心理学上画人物侧写的方式,拍一个连环杀手的杀人模式和背后的心理,放弃传统叙事的情节性,转向去给一个时代的德国社会画肖像,纳粹们老了之后只剩肥胖和丑陋之后,导演最后给了他们一个这样的下场。★★★☆
Hell's Kitchen,这便是这家名叫[金手套]的酒馆的真实名字。隔着银幕你就可以闻见电影里面的恶臭,中间混杂着酒精味、呕吐味、血腥味和尸臭味。阿金对场景的拍摄异常纯熟,演员的表演、特别是女演员们岂止是鲜活二字可以形容。但影片最后沦为猎奇之作。剧本把原著小说里关于主角悲惨过去的部分全部删除,导致整场暴力尽显荒诞和机械。这样的决定使得电影中的暴力表现出平庸和无意义无原因性。但同时影片里又有与70年代既不符合的当代场景,似乎是为这样的暴力寻找源头:无论彼时还是现在,这些人都是社会繁荣背后的失败者。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矛盾。此外这些当代场景尽管是由于资金问题而做出的无奈之举,但如此的逆时性让整部电影显得风格不一。
人如果像动物。。。导演复原的太一致了真实的仿佛就在身边发生的
粗俗一点讲,“金手套”酒吧是块腐臭的烂肉,供养着社会蛆虫,靠酒来麻醉自己肮脏的灵魂。男主洪卡蛆虫中的佼佼者,做着“吃鲜肉”的美梦,吃着恶臭的腐肉,理想和现实冲突时,就变态了,嗜血了、泄愤了。今村昌平说“我将书写蛆虫至死方休。”《金手套》大概就是属于“蛆虫”电影这一类。
穷与富在炼狱般的《金手套》里不是以物理意义上的财产来划分,而是用道德上的美丑来区别。二者的位置刚好与《寄生虫》相反:丑陋猥琐的变态杀手盘踞上层,美观体面的中产家庭栖居楼下。作为滋生和孕育恶之果的空间,尸臭与浮蛆皆是自上至下令人无法逃避地扑面而来。人物在阿金这部讲述罪与罚的寓言里是抽象化的符号,影片借着案件试图分析阶级斗争的根源。他认为问题在于现代宗教的神秘面纱最终被幻想落空后的事实揭穿和识破,如醉如痴的无产者意识到“阶级交替”这份协议本身的虚假性和欺骗性。货币在这个犹如社会的酒吧里要换算成以瓶、杯为单位的酒水。既是“猎人”吸引“猎物”的诱饵,也是“强者”施暴“弱势群体”的终极武器。最终只有极少数幸运的人被“上帝”救赎,听命道德的“魔鬼”追随“天使”到了深渊,绝大多数人都被那条火舌迷惑和吞没。
嘘,你隔壁那个又脏又乱又臭的房间,可能就住着这样一个性压抑兼性变态的男人。而那个又老又丑又肥女人眼角的泪水不知哪天就滑落到你起皱的嘴角。
全员神演技。今年看过的最生猛的犯罪电影,原始,兽性,真实,颓废,一群被酒精控制的行尸走肉,二战后一个信仰缺失的国度,阿金有点一片封神的味道。
如果说「此房是我造」是精神美学犯罪,此片就是另一个极端。物尽其用展现德国70年代战后遗留底层生活的混乱萎靡,年代感烘托,甚至每次受害者疑惑屋中腐臭味都可感同身受,整体观感倒并无不适。强悍在于看片尾案件照片才知还原力有多强悍,演员化妆与演技也值得称赞。
在一水儿苦大仇深剧情片的柏林,我一直特渴望看到一部血浆暴力片换换脑子,这不就来了。影片塑造了一个地狱般堕落和放荡的70年代,酗酒嫖娼留级失业,凶案无人问津,人人得过且过,像金手套酒吧一样永远遮住窗帘看不到阳光。我很喜欢这部片统一的内在气质,肮脏、肥腻、令人作呕,血腥适度,幽默少许。我也喜欢卡西莫多一样丑陋男主的塑造,在最后的长镜头里,金发美人悠然离开犯罪现场,他们从未发生过交集。片尾PO出几乎一模一样的真实罪案照片,很震撼。演员特效化妆也蛮牛的,完全看不出痕迹。
1.0 / 不太明白早年能拍出《勇往直前》的法提赫·阿金为什么现在会flop到这个地步。只有空洞的概念意义和切片的动作(注意,是动作,而非仅仅是暴力)展示谈何触碰历史和现实?难道只是因为男主被化妆打扮得比较像Hitler吗?那建议直接凭定妆照入围柏淋电影节呢。
2.5
Weil die Jahre viel zu schnell vergehen/Und weil dein Junge einmal groß sein wird/Denk an die Jahre, die noch vor uns liegen/Vergiss den Tag, der mich einst von dir führt
朗·钱尼与德国表现主义在此同法斯宾德室内剧一起被强行架空赋予了空间调度蹩脚的现代比喻,电影涉足的庞大历史症候无法和这起本身已经足够惊骇的个体样本事件相融并被强调出来,或者说是特定的点对面指向的无意义,只看到了一个庸才哗众取宠的电影节自我标榜炒作。
前期各路“呕”的观感评论把期待拔得太高,结果成片就没几分钟,且尺度不大,全程失望冷漠脸。在道德观念上,甚至还没《凭空而来》一半来得勇敢惊艳。个人觉得本片文本上的过度空泛、不扎实,可能是阿金根本就无意于回溯二战、70年代社会问题等角度,就是单纯随随便便拍个这种片子——某种意义上和《系统破坏者》倒是殊途同归,水平高一段位罢了。查了下乔纳斯·达斯勒竟然这么小(和我同龄),无语,叹服。
还原了七十年代汉堡红灯区连环凶手弗里茨•洪卡以“金手套”酒吧为据点将四名妇女猎入自家阁楼公寓并将其杀害分尸的经历。导演极力刻画由憎恶女性、性贪婪和多愁善感所驱动的施暴者的堕落肖像,摒弃了诠释性的背景补充。风格上不乏对法斯宾德室内剧的借鉴,且尤以长镜头无节制地展现暴力,同时以塔伦蒂洛风格介绍配角,成为对告别经济奇迹不久的西德社会反面的环境研究:在毫无希望的阴暗德国,战争毒瘤和战后混乱令个体生活彻底受阻。
其实制作挺精良的,服化道演都属上乘,而且所谓的大尺度也真没觉得恶心,感觉大家都有点误会阿金了。男主复杂的性格成因正是创伤症候的绝佳展现,性无能、酗酒、暴力、肢解,导演不仅通过给杀人犯著书立传来替战后遗毒和虚无主义招魂,而且还借男主的手亲口剪掉对方(时代的受害者)的舌头(拒绝历史和解与沟通)。有趣的是,年轻的小男孩闯进时代的弃所,他以为见证了一丝怀旧的轮回,没想只是惹了一身骚。最后的一场大火,漂浮在夜空上的鬼魅之烟,是德意志时代冤魂的集体控诉,于我而言,或许这才是导演“变态”背后的善良底色。而最终的真相就如那个金发女孩的转身而过,她只是与历史的断痕打了一个照面。
你所见到的丑陋,只是世间一晚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