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在高速發展的中國,像蘇這樣的流浪者的生存空間已經越來越小。在杭州一條正在建設的二十四號大街旁邊,蘇和情人琴開設了一家簡陋的餐館,但因為沒有經營許可證,他們和其他一些非法住戶總是受到政府的驅趕,處世不驚的蘇和琴在另外的地方又建立起一個自己的餐館,但不久又被政府拆除。蘇決定回到故鄉,那裡有著他曾經的家庭和兒女,同時也有著琴的家人。但是已經在外闖蕩了30多年的蘇,家人對他的到來並不歡迎。導演通常默默地觀察蘇和琴的歷險,但偶爾也會介入,當蘇開始有不道德的行為欺騙他人時0.24號大街有著豐富多彩的主人公,影片展現了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的轉折,和那些追趕不上這個國家飛速發展腳步小人物的故事。 China doesn’t have a lot of room anymore for peddlers like Su. He set up a ramshackle restaurant next to a construction site on 24th street in Hangzhou, but of course he neglected to obtain a permit. Unsurprisingly, the authorities send him and the other illegal dwellers away. Unfazed, Su and his girlfriend Qin find another place for their restaurant, only to be sent away again. Su then decides to go back home to the countryside, where his wife and children, along with Qin’s family, still live. After being away for 30 years, the couple isn't exactly welcomed back with open arms. Filmmaker Zhiqi Pan usually observes Su and Qin’s adventures without comment, but does step in on occasion, such as when the unscrupulous Su is trying to cheat people. With its colorful main character, 24th Street offers an original twist to the story of modernizing China—and those on the fringe who can’t keep up.陌陌影视陌陌影视樱花影院6080影院千夜、一夜生前约死后王媛媛水墨人生第二季真实故事改编第二季前进天堂2002柯林·奎恩:红州蓝州浪漫面包屋电竞高校不思议游戏OVA3:永光传老处女1939血色土地 第二季不羁的美女国色芳华玻璃樽国语苏夫塞德女孩第一季行尸走肉第二季大明帝国 第二季怪谈新耳袋 消灾求福也没用篇石榴坡的复仇都柏林凶案龙凤配永远的北极熊告别摩门第一季恋与枪弹
长篇影评
1 ) 写在都市塑料澡盆的边上
本次金马影展的第一场,就从2018/11/8的《24号大街》开始了,作为平日的中午,上座率蛮高,观众层从年轻人到老年人不等。
我蜷缩在座椅上,观看老舒(ps:从影片中的“舒记小炒”可以知道是舒而不是苏,但是字幕都写作苏,不知何意)夫妇的近十年。
没有倒序,就是很平铺直叙的开始,锁定了在杭州24号大街开工前夕的棚户游民一员老舒夫妇,从贵州来到杭州务工,在暴雨的夏夜,依靠着铁架和塑料布支起的“房屋”,靠着向施工工人出售农家小炒来维持生计,时间定格在2010年,距今10年前。初次出现在镜头里的老舒没有我一贯印象中所要拍摄的底层城市群体的心酸和沉默,反而显示出一种朝气,对生活的热望,他谈起自己的打算,说到自己的生活都还颇有兴致,乐于分享,脸带笑意,也许很多人觉得不以为然,但是我反观身边的正值青春的高校学生,其实有这样积极面对生活者实在寥寥。
可是因为24号大街的兴建,棚户区迅速拆除改造,镜头短短5分钟,老舒的阵地就随着一辆搬家卡车搬去了不远处的一片荒地,真的是荒地,他和琴姐两人铲平土地,徒手安装铁架,搭起塑料布,两个人的力量居然在那么快的时间搭起一座暂时居住的三居室,可是简陋到好像在寂寞无人的荒岛上开荒,而这偏偏又发生在长三角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里,电影里城管有一句话说“高楼大厦的人一眼望下来,看到你们这些破破烂烂的棚户区成什么样”,有些凄恻,一个人的生活 居所已然是因为高楼者的眼而不可存在。此时已到寒冬,老舒和琴姐伴着一犬在“新家”挂起了小餐馆的招牌,虽然应者寥寥,可是老舒比谁表现的乐观,他说人气是慢慢积攒的,一个月没有积攒到人气,却被告知要拆迁。
在多次的协调无果之后,老舒带着琴姐回家了,本来我只以为是城市劳工一无所获的返乡故事,结果老舒在贵州老家还有少时婚配的没有感情的妻子,妻子独自抚养儿女都已结婚生子,而琴姐则是30年前打工相识等等,回到家中,面对难以调停的感情问题,面对琴姐家庭的抱怨,面对自己子女对他这个父亲角色一直以来缺席的怨恨.....都挤压着老舒,没有出口,也没有头绪,他也曾做过努力,从中调解,去政府申请补贴项目,徒劳无果。
在一番挣扎之后,还是和琴再一次回到了都市,这次选择的是无锡,也许找到了新的活计,也许没有,但是看上去生活是好了那么一点,尽管微不足道,老舒又燃起了热望,想着赚钱,再给琴姐买套房子。
画面再次出现时间标识,已经是2016年了,老舒来看望杭州务工的儿子,居然巧合的也是24号大街,此时这里已经是成熟的商贸区,他站在十字路口,向拍摄者认真回忆自己房子的地方,记得那样清楚,才让人觉得心酸。
想说几个重要的物象吧
1.红色澡盆。老舒说自己不论去哪不论多累,都要每天泡个澡,就在那个促狭的红色塑料澡盆,用的是凉水,很短,要完全蜷缩在里面,好像是小孩子用的,年近50的老舒躺在里面很滑稽,可是这个澡盆他去哪里都带着,就算在整洁的路边,西装革履白领走过的时候,老舒还是穿着格子短裤悠游自在的泡澡。
2.财神。老舒一直在说赚大钱,发财,我想在场的观众一定要笑,他这样能够活下来保存温饱都不容易了,怎么还会痴望发财。可是老舒那么真诚的盼望,也那么真实地笃信,而且把他当做房间里必不可少的存在。我看到这里,就觉得老舒真的是热爱生活的人,试想我考着年级倒数,还会时时刻刻把北大贴在桌上吗,老舒总有一种期盼,不切实际的期盼,可是在这样的磋磨下,还能保有这样的期盼。
3.老照片。老舒在落魄的窘境下拿出年轻时和地方领导的合影,说起自己当年也是做工程年入百万的主儿,要不是领导倒台,自己连带赔钱,又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无法辨别老舒此言的真实性,照片模糊也不足为证,可是他这样朝不保夕的生活,行李能省则省,这些照片却一直带在身边。也许是真的,是对过去峥嵘岁月的不舍,每每示人,倒也是“我祖上阔过”的凭据,也许沦落至此,也是在努力为自己争取一些尊严。
观影之中,我从最开始的同情,到对zf的愤慨,又联想到天下之大,居然让这样一个合法老实本分的公民无立足之地,到最后的反思,也许老舒这样的城市边缘者的身份让我们对他带有很多本能的观感和应有的情绪。可我却从中看到了一个“人”的内核,就是被生活挤压到变形,可是精神内核依旧健全的人,他比我们身边更多生活优渥的人,更有一个“人”的样貌。他相信未来,也肯吃苦,相信总有出路。重情义,一心还想为那个跟着自己多年无名分的女人买套安身之所,争执着怒骂着,却还是会笑起来,我当然无意标榜这样的心态,也不是要鼓吹什么正能量,恰恰相反,也许就是在这样的不断挤压中,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努力调整的心态,说到这里,就让我想到梁文道在评价《活着》的时候,说中国人就是这样,就是活着,活着就好。
十年过去了,24号大街改变了,可是老舒的现实处境没有改变,依旧被驱赶,浮在这个繁华的都市之上,飘着飘着。可是与此同时,人却妥协了,茫然地走进地铁,带着笑去看望再一次在24号大街务工的儿子。
时代不是10年前了。老舒的儿子还会面临和老舒一样的困境吗?
2 ) 城市化并不是你无家可归的借口
一个小人物—苏永禾由于城市化的进程被迫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他可以和情人在杭州简陋的工地棚户生活下去,但是随着开发的进行,不得不离开杭州回到老家,以前欠下来的账终究要还的,他本来可以回家养老,但他这么多年不给家里一分钱还搞了外遇,这是他老家的妻儿无法容忍的,他不得不又回到杭州继续他的流浪生活……
真的是城市化使他流浪吗?!我觉得并不是。是他对家人不负责,他的自私自利使他流浪。他既然选择了和小老婆一起生活,就要做好回不去家的准备,还带着小老婆回老家,想一起生活, TOO NAIVE!他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后路,只能咬着牙,继续过着流浪的生活。😏




3 ) 流浪汉的歌谣
我看的是日本NHK剪辑版,总共仅有49分钟,很多场景都是匆匆而过,没有完整剧情,能看到裁剪的痕迹,大致看出故事脉络,这一版算是匆匆一瞥,但也足够惊鸿。
老苏有着中国农民的狡黠和矇昧,在流浪的过程中,磨练出了不得已的生存智慧。他懂得利用镜头,他流浪30多年,和社会和家庭有着深深的摩擦和隔膜,他辗转多地,从杭州24号大街,到江苏无锡,再到贵州安顺老家,再又回归杭州,可以说这一路的辗转,是和社会的摩擦和对抗,最终节节败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回归老家之后,和家人的冲撞,妻子的冷漠,女儿的谩骂,这样一个漂泊的灵魂,流浪的孤岛,终究被一步步又推回故事开始的地方。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人不离不弃,他是老苏的情人,陪伴在身边,所以,他要给情人买房,要和情人孤独终老。
最近读到余华写给《活着》的自述,余华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和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我的理解就是一种悲悯,一种超然是非和善恶的悲悯,这样的情感高于一切。
影片中有几个场景让人印象深刻,一个是和女儿吵架的镜头,当女儿各种抱怨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老苏内心的撕扯和无奈,作为父亲自然是不及格的出门这么多年,女儿的人生和成长,他是缺席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一个是老苏在城市的自来水阀门洗澡,一个足以装下他自己的塑料大盆,不管走到哪,他都带着。另一个场景就是片尾,当老苏再次漂泊,再次东山再起,他在一所荒原,身外什么都没有,只有情人和几件旧家具和四个空空的柱子陪伴着他。
西安的大马导演曾经给我看过一部他自己拍的关于工地的纪录片,他很低调,随便拍,镜头下的人物非常精彩,至今让我印象深刻。拿部影片也有无数个老苏,各个都是那么的鲜活,他们是流动的建设大军,每一个城市的高楼大厦背后,都有无数个老苏的故事,他们有的没有身份证,他们背井离乡。
4 ) 阅读自己的症候
我在看片,也在看自己。
为什么琴会跟着老苏呢?我不是琴,我当然不知道。但是我看到的是,老苏是琴所见范围内最合适的对象,即便没有名分。琴受到一些家暴(导演见面会上说的)离过婚,即使走南闯北住棚屋也跟着老苏吃苦,一走就是二十几年。
另外,琴是崇拜这个男人的。相关部门要求老苏在10天内拆除刚刚搭好的棚屋,这可是老苏在工地辛苦挣来的4000块钱材料费,一纸命令后老苏想重新开起小饮食店的兴奋性瞬间180度转变得极为急躁,怨天尤人,感慨天地之大毫无容身之处。过了几天,老苏将这个还未拆的棚子以6000块租给另外的农民工,然后离开了这座城市。虽然这是这个男人有狡黠的一面,但无疑是生存之道。面对不可抗力:)只能将风险转移。呵,男人,你行!
老苏的小餐饮店(给农民工吃饭的棚屋餐厅)营业没有许可证,被相关部门拆除,老苏认为自己天经地义,怎么就违法了呢?我觉得,世上有很多东西,的确是会超过自己的心智/知识范围,面对“圆”之外的心智/知识人就是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并且,强行认为自己有理,殊不知“理”只是“圆”中的理,“圆”外也有理。
老苏回老家为什么赶不走(离婚)原配芬,带琴进门呢?芬为什么能容忍老苏?用情感是解释不来的,用经济学的思维应该能说的通。芬和老苏有两女一子,儿女是芬抚养长大的,苏只给过很少的抚养费。芬在这个家庭中的角色是养儿育女。琴呢?她陪伴老苏在外闯荡,是老苏事业上的帮手。因此,老苏的妻子是应该有养儿育女和事业帮手这两个身份的。芬和琴都只占了一半。因为老苏享受了这两个角色带给他的收益,他就应该回报这两个人,而不是情感决定我想离婚娶琴。芬虽然很没面子很气恼很无奈,但是她完成了这个角色,她就应该咽这口气。
这个片子没有戏剧性,一切都是理。因为社会秩序就是这样,阶级、伦理是这样。
我和老苏的生活环境很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在这样的秩序中,老苏是我,我是老苏,我是琴,我是芬。
5 ) 金马奖纪录片遗珠《24号大街》| 流浪夫妻被驱赶中挣命的30年

11月17日晚,第55届金马奖在台湾举行,被誉为华语电影奥斯卡的金马盛典再次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青年导演潘志琪的《24号大街》提名了“最佳纪录片奖”,收获众多好评。
该片聚焦于一条杭州下沙区的24号大街,和中国所有正在重建的街道一样,正在等待以全新面貌示人。
这些街道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务工人员,他们搭建棚户居住,通过开小饭馆和卖东西谋生。

杭州下沙区

傍晚的棚户区,冒着饭菜的热气
当青年纪录片导演潘志琪搬到这里时,他的目光锁定在了这些底层小人物身上,拍摄了七年,积累了三四百个小时的素材,最终融合成了一部纪录片《二十四号大街》。

这部纪录片也入围了第30届阿姆斯特丹电影节(IDFA)长片竞赛单元,是唯一一部入围的中国作品。它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也拍下了在大时代中挣扎生存的小人物。
1
当代农民工困境
进不了城市,回不了老家
老苏,60岁农民工,来自贵州农村,他和女朋友琴住在24号大街的棚户区。

老苏和琴
年轻时就背井离乡四处打拼,东北三省创过业,新疆阿克苏淘过金,他曾这么说:“生活要想开,能吃吃能喝喝,有机会要到世界周游一圈。”
老苏也确实像周游世界一样过着自己的日子,一辆小三轮上拉着一张大床,走到哪里就以大床为中心搭建一个小棚屋。
他和琴在工地上种菜,开了个小餐馆维持生计,光顾的客人都是棚户区周围的务工者。

狗狗也是简陋小饭馆的常客
说到感情经历,老苏也算是个奇人,以前在老家是包办婚姻,为了逃离没有感情的生活,老苏和琴选择到大城市闯荡。
老苏还有一个红色塑料澡盆,闲暇时他就在路边用消防水泡澡,全然不顾路人的眼光,他说:“这个澡盆子走到哪里都带着,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2011年,24号大街的棚户区面临拆迁,这里马上就会有一个新小区,还会有五星级酒店拔地而起。
老苏和琴以及附近的工友们,只能收拾家当,搬到城市里更加边缘的郊区,重新搭棚屋,重新开饭馆,重新招揽客人。
搬离前一天,老苏和邻居喝着酒,邻居无奈地说:“你在这里开小饭馆没有营业执照,执法大队要你滚蛋,你就得滚蛋。”
老苏喝了一口酒,愤然说着:“这到底是执法还是违法?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又不是难民。”


虽然想不通,虽然愤愤不平,但也无计可施,最终老苏和琴搬到了一块新荒地。几根竹竿,几米帐篷,几张木板,开始安营扎寨。
白天,老苏靠着打扫卫生、清洗下水道、修剪道路两边的草坪,赚取微薄收入;晚上,数着零零散散的钱,他开始规划自己的小饭馆。
赚到4000元后,他的小饭馆开张了,按照江湖规则先请了财神保佑自己开张顺利。开张前几天生意冷清,但老苏也很乐观,他觉得做生意就是这样,不能急要慢慢来。

漫天大雪里,老苏和琴看着远方,对于他们来说未来太遥远,能有个养家糊口的生意就不错,能有个遮风挡雨的棚屋就该知足了。
然而生活的打击总是来得很突然,城建执法大队又来了,要求老苏和琴20天清理干净违规棚屋,否则就要进行强拆。
这一次,种的菜苗被压坏了,施的化肥打了水漂,老苏找人理论,要求赔偿未果。

30年奔波在外,俩人已经累了,年龄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老苏和琴选择了一条路——回老家。
他把自己即将要被拆掉的棚屋卖给了别人,拿到钱之后的老苏看起来有点狡黠,这是小人物被生活挤压出来的精明,这是他的江湖法则。
2015年,老苏和琴回到了老家贵州,这个小城也在飞速发展中,修公路、修高铁、修高楼,同样面临着拆迁重建。

老苏的家乡也在重建
长年漂泊在外,老苏对土地已经陌生,无法下田种地,他失去了谋生技能。
同时,早年“抛弃妻子”缺失了孩子们的成长,老苏和家里产生了无法修补的裂痕。
坐在家里的他,尴尬不安,原配妻子和他除了吵架一句话都不说。在亲生女儿眼里,老苏不配当父亲,他是一个罪人。

大女儿责备老苏
不仅老苏的妻子和孩子接受不了老苏归乡,琴的父亲和弟妹也同样难以认可琴和老苏的这段感情。
夹缝中生活的老苏真的很难,他还去政府咨询了创业扶持项目,为了不委屈跟了自己半辈子的琴,他还想给琴买套房子……


从农村走出,在城市中辗转,又因为被城市驱逐,回到农村老家。
老苏和琴不断的迁徙,就像千万个农民务工者的处境一样,在城市里无法立足,但又回不到故土。
《二十四号大街》的最后,老苏和琴还是背上行囊继续外出奔波,他们来到24号大街看望打工的儿子(老苏的儿子),站在高楼林立的全新的24号大街,他们看起来那么渺小而迷茫……

片中有一段介绍是这么说的:“曾经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已经跟不上发展的节奏,被这个时代甩出去了。”
这是导演潘志琪想通过纪录片表达的“大时代”和“小人物”的故事,这一切也让我们反思:
现代化城镇化飞速发展的进程中,一些群体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如何保证? 十年二十年后,这些群体的下一代还会面临和他们的父辈一样的困境吗?
2
现代化飞速发展
底层小人物如何生存?
为了更加深入了解《二十四号大街》背后的创作故事,DOCO君对话了导演潘志琪,于是有了一场更加深入细腻、别开生面的交流——

D:DOCO君
P:潘志琪导演

潘志琪纪录片导演,浙江传媒学院电视艺术学院副教授,曾就读于西安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艺术硕士。纪录片作品有:《侦探》、《迷墙》、《二十四号大街》、《胡阿姨的花园》(制作中),选题聚焦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中大时代小人物的生存命运。《二十四号大街》入围第30届阿姆斯特丹电影节(IDFA)长片竞赛单元、获评第2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IDF)优秀纪录长片、提名第55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D:我想先问一下片名的由来,有些观众说老苏和24号大街的故事只在片中呈现了1/3,那“24号大街”这个片名是否只是一个意象化的表达?
P:其实是一种意象化表达,这个片子开始2010年是这条街和棚户区,结尾时候2016年还是这条街和高楼大厦,所以它有个时间的跨度,然后也有时间上的对比。同时这条街和6年来老苏他们这群人的家庭故事也可以形成参照,所以它是意象化表达的意思。
D:它就是开头和结尾有了一个互文的效果。那现在中国城市化进展特别凶猛,您的镜头是怎么锁定在这条街和老苏这个人物身上的呢?
P:我觉得机缘巧合吧!我刚好是纪录片导演,就一直关注这样的事情。我搬到这里时,一开始就是破破烂烂的棚户区吸引了我,然后慢慢在我进一步了解这个人物、了解到老苏这几十年生活经历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其实只是拍一条棚户区,它的表达、它所承载的东西可能会少一点,所以我想把这个跨度拉得远一点。当老苏跟我说起他要回到老家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把这个跨度拉到东部跟西部、城市跟农村,所以就形成了片中的结构。
D:他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很多群像(农民工、边缘人物群像)里边的一个具象化的体现。
P:对对,一个个体,比较特别的个体吧!
D:他这个人物特别立体,包括他有那个纯真淳朴的一面,然后也有特别圆滑世故的一面。我记得有一个情节是本来他的餐馆(棚户区那个餐馆)要拆了,但他转手又卖给了另一个人。他这种行为的话,您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怎么看待?
P:其实我们拍这个人物不是去选一个道德标兵,我觉得人物的多面性(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这样的人物才是真实的个体。
D:嗯,一个完整的个体。
P:对,而且我觉得像艺术创作,或者说一个电影的人物不能很单一、很概念化去把他想象成某一个英雄。老苏也希望在我的镜头面前呈现他英雄的一面、好的一面,但我恰恰是在把他往回拉,希望他能很真实,他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D:其实咱们也都知道,每当镜头对准自己的时候,多少会有一些表演的成分。您作为导演,觉得拍到的主人公老苏就是最真实的老苏吗?
P:我觉得不全面。我们希望去了解真实的世界,恰恰片子里永远是去接近真实,它是不可能完全百分百真实的,所有的东西都呈现出来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和多方面因素有关系,一个是拍摄对象,他肯定会有他保留的一面,同时从艺术创作和纪录片的构成上来讲,你也不可能完全去呈现所有的真实。它跟创作本身也有关系,和每个导演、每个摄影师的主观性也有关系。
D:他有没有拒绝过拍摄?您和他怎么沟通,包括跟他家人的沟通?
P:不仅仅是他,所有的被拍摄对象都会有主观性的、想介入导演的思维。他总在想象这个片子他希望呈现的一个模式,当然我之前一直在跟他说“我不是要把你塑造成英雄一样”,我一直在给他做这种工作。
D:就已经给他打了一个预防针。
P:对,包括他说这个时候可拍那个时候不可拍,也不能完全听从他的,在拍摄过程中确实有些时候他是会拒绝、会回避的。
D:那他现在的生活状态,他还是在和琴四处漂泊吗?
P:他现在生活稳定了一些,到无锡进了工厂打工,相对来说稳定了一些。
D:因为城镇化的发展,社会空间和人物都有变化,您怎么通过镜头展现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和状态?
P:这个片子做这么多年时间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只有通过这么长时间长跨度的一个参照——一条街的变化跟一个人物的这几年的生活,最终来给出我的态度和观点。
D:就是在社会洪流之下,其实大家都是努力活着,尽自己所能。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判断他们,就是你怎么不这样不那样,有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感觉,也不能用道德标准去束缚他。
P:道德标准这东西怎么说呢,其实我刚才已经讲到了,片子中的这种人物,包括纪录片的人物也好,剧情片的人物也好,其实我更倾向于去表现人物更为复杂的人性,这样他呈现、折射出来的社会的很多方面也更有趣一些,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些,而不是非常单一的、非黑即白的这种关系。
D: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世界,他这种人物的多元化也映射出社会的状态。那咱们这个片子也在金马奖提名了,您有什么样的预期、预判?
P:就随它吧!因为这个很难说,好片子都挺多嘛!看评委的口味啊!我觉得随缘就好。希望大家喜欢片子就好,或者说片子可以带给我们对当下社会更多思考,那我做这个片子的目的和意义就有了。
D:您个人想通过片子传达和传递给观众的东西是什么?
P:其实就是希望通过老苏这样一个故事让大家去思考快速发展的社会里怎么去考虑这样一群人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权利。
D:关注到更边缘化底层的群众的一些生活。
P:其实我可能跟他们比较熟了,我从来没有把他们认为是底层,我就觉得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只不过他们的收入没有中产阶级那么高,但他们是社会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D:您之前在映后也说过,时代的年轮向前发展,他们也是注定要被留下来。
P:目前看是这样,其实每个时代都会有这种现象,就是随着一个时代的到来,另外一代人,或者一个群体,他会进入新时代的挑战,那么在这种挑战过程中他可能会被慢慢淘汰掉,或者面临转型等等。
D:您怎么看待纪录片的艺术创作形式?它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P:我觉得纪录片它呈现的东西会更直接一点吧,包括它会有无法回避的很多现实的问题。
D:您未来的创作方面会考虑比较尖锐的话题吗?
P:我觉得其实做这些选题还是跟导演的态度和机缘有关系,你碰到了一些话题你能把它拿下来,那当然就不要去回避它。每人做选题其实还是跟自己的圈子,跟你碰到的东西有关系,有些东西是不能强求的。
D:您希不希望纪录片更商业化?
P:不回避商业化,但是目前的市场环境来看,比如说这种直面现实的题材要进入院线,我觉得可能大众的审美或者是大众的接受度,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考量。大家可能不愿意去面对一些真实的东西,可能不愿意去面对真正困扰我们的问题,更愿意去畅想好莱坞式的、梦境式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是跟当下的审美,或者是跟电影文化的消费方向有关系。
D:您后续有什么拍摄的方向可以跟观众透露一下?
P:拍重庆的《胡阿姨的花园》,基本进入后期了,讲重庆十八梯的。它在旧城改造,已经拆的差不多了,正在原来的基础上开发新的商业区。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截图
采访 | KK & 婧哥哥
摄像 | 糖糖
编辑 | 婧哥哥


6 ) 用尖利的牙齿咬碎一切粉饰
《二十四号大街》解析:用尖利的牙齿咬碎一切粉饰
一、《二十四号大街》概述
纪录片《二十四号大街》的导演潘志琪是浙江传媒学院的老师,他历时7年从 2010 年开始至 2017 年成片,辗转于杭州、苏州、贵州三地跟拍的苏永禾的漂泊故事,整个纪录片都按照老苏的漂泊过程展开叙述。《二十四号大街》入围过去年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DFA)创立于1988年,是欧洲最大的纪录片电影节和纪录片市场,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纪录片电影节之一,被誉为“纪录片界奥斯卡”。并且在今年的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上,《二十四号大街》还获得了IDFA优秀纪录长片。
在影片的叙事中,影片一开始为了点名主题,放置了杭州市城建开发的镜头。接下来就是老苏因为拆迁而辗转几个城市搭棚做“无证餐馆”。影片中间有两个具有冲突性的情境,一个是老苏在离开原本的地方后又被要求离开时给市委书记黄坤明打电话的情景,还有一个是老苏回老家后与女儿的争吵情景。这两段情节表明,老苏实实在在是一个漂泊的人,城市无法容忍他,他也无法回到那个他出生的地方。影片的结尾,老苏离开家,又开始了漂泊的生活。“漂泊”二字贯穿始终。
本片2017年在NHK电视台播放过,它的副标题就是《中国流浪民工的故事》。根据2018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调查的数据。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达到1.74亿人,同比去年增长了1.1%;月均收入达到3736元,同比增长了7.3%,本片的主人公苏永禾(以下简称为老苏),就是上述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总体月均收入上升,但却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个月都能拿到这3736元,还有很多人在温饱线上挣扎,本片的主人公老苏就是在温饱线徘徊的一个人。老苏是时代洪流中被卷起又抛下的人,导演潘志琪这样评价他:一开始观看影片时,观众可能会以为老苏似乎是一个幽默豁达而又玩世不恭、唯利是图的人。但是看到后面,你也许会怀疑你一开始的“界定”或“判断”。当你进入到他的处境时,这个“界”便开始模糊、甚至被打破,你也许会重新认识老苏这个人物的复杂性。
二、叙事方式以及结构
整部纪录片采用了线性结构的叙事方式,影片内容层次之间有比较鲜明的时间顺序关系、因果关系与递进关系,按照老苏的漂泊过程的自然次序来组织、安排素材,脉络清晰,结构单纯,简单易懂。观众对其最直接的观看体验就在于它扑面而来的真实感,全片似乎只是将生活的横断面照搬进荧幕,未经任何人工雕琢,严格恪守了格里尔逊对于纪录片真实本性的追求。这种再现现实手法的成功运用,很大程度得益于纪录片创作者在影片叙事视角上采用了热奈特所提出的外聚焦式的叙事模式。在这种客观的叙事视角下,潘志琪作为叙事者等同于没有感情的机器,只表现影片人物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事物,不作主观评价,也不分析人物心理,只是客观展现了七年间老苏从杭州——无锡——贵州——杭州的漂泊过程。
在整部影片的时空结构中,导演潘志琪以跟拍的路径展现了整个影片中的空间变化,如下图所示:

在空间变化中的移动路线及原因:
(1)浙江省杭州市市内移动(2010年):杭州市内城建开发,政府通知老苏从原来的棚区搬走。
(2)江苏省无锡市(2014年):又因为公司开发,与公司老板、市委书记斡旋不成,他和琴从杭州市搬到了无锡市一块新空地。
(3)回老家贵州省安顺市(2014年底):老苏说自己不想再流浪了,老家也因为高速路工程的开发要拆迁,会有一笔拆迁款,他卖掉了原来的棚屋,借扫墓回家,想在老家用拆迁款重新发展。
(4)浙江省杭州市(2016年):由于家中的矛盾无法解决,老苏决定重新出发。影片最后最后老苏来到了杭州探望在二十四号大街工作的儿子。
这样的空间变化形成了一个闭环,老苏从贵州老家出门漂泊,中途回到贵州。他从杭州出发,最后又回到杭州。这是老苏的闭环,他永远都在游离,却没有定所。而他回到杭州的原因是儿子在杭州二十四号大街工作,也暗示着儿子将从这条大街出发,很可能会重复他的生活,这是一个环形的结构收尾,这是生活与生命的闭环。这个闭环暗喻这不只是老苏,还有很多的边缘群体的人,他们很难或者说无法打破某些身份与阶级的壁垒,逃离这样的生活,这本身也许就是导演对社会阶级存在、阶级流动固化的一种反思。
除了老苏在实际距离上的移动空间,还有老苏他们与城里人在心理上的空间距离。中国从1950年开始实施户籍制度,它根据血缘继承关系和地理位置,将户口划分为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这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村与城市之间出现了隔阂,形成着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其实是一种不公平的等级界定,它带有一定的歧视性。所以影片中通过实际空间距离展现出了城乡二元的空间结构,也隐喻着城市人与农村人在心理上的距离,老苏作为个体在城市与农村的空间之中游离,没有栖身之所,反映着中国农民工群体在中国的生存现状。
在时间变化中:
除了空间结构,导演表示,在《二十四号大街》这部作品上,他希望能用时间的跨度去看这条街的变化,以此参照人物的命运。在这部影片中,最为明显的时间线是作者跟拍的七年时间,老苏的流浪旅程与中国发生变化的自然状态时间,七年中,老苏和琴在杭州、上海、贵州之间不停的兜兜转转。而在这其中导演又通过老苏的人生故事表现出了在影片中隐藏的时间线,也就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的快速发展过程。老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来闯荡到现在(影片中的2010年)与中国三十多年快速发展的时间正好吻合,但他却也正好与中国的快速发展脱节。从这条隐藏的时间线可以看出,这就是导演所想要表达的大时代与小人物这一对矛盾的凸显。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在发展的几十年中,中国已经有8亿人民脱贫,他们根本用不着担心温饱问题。但同样是在这中国发展最快的三十年,几十年的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从城市的“奠基者”沦为了城市生活的边缘化群体,老苏可以看做是大时代背景下的一个缩影。总的来说,导演通过对空间与时间的描摹,通过对细节的展现,对照出了大时代下小人物的生存现状。
三、影片中的故事性
这部纪录片围绕着苏永禾这个“小人物”展开了叙述,人物本身的矛盾性与冲突性和他的流浪旅程构成了本片较强的故事性。一个就是体现在老苏本人的人生故事上,另一个是他的流浪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首先老苏有着极为复杂的人生经历与家庭关系,是一个特殊个体。潘志琪接受采访时说:“其实我一开始调研了很多人物。慢慢地才觉得老苏身上有很多我想要诉说的东西。我希望能够透过老苏、透过这部片子来表达我的一些态度或者观点,包括他与这个时代的一些关系以及我在其中的一些思考。”他表示,当初选中他拍摄也是因为觉得老苏有人性中复杂的东西。老苏八十年代在跟着领导做三峡工程时由于领导倒台赔了一百多万,从此一蹶不振;他不满于包办婚姻,因为重婚罪和超生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后,与女友琴踏上了流浪之旅,他说琴是个吃苦耐劳的人,愿意和他一起闯荡江湖,但最终他们一事无成。
在老苏的流浪旅程中,他辗转了4个地方,在搬迁时会有一些冲突存在,在他将要离开无锡的时候,他将他的棚高价卖给了别人,但这个棚区不久后就要被拆掉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老苏有些唯利是图,这些许多的冲突的碎片构成了整个纪录片的故事性,使得老苏的人物形象更加具体,并且能够调动观众情绪。还有他在第一次被迫搬迁时被政府驱赶,在第二次搬迁时被开发公司驱赶,他说,“中国这么大的地方,960万平方公里,都没有我的立足之地。”这几句话深刻地描绘着本片的主题,小人物在偌大世界中的无奈。他们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如果生活漂泊无依,人生是否还有理由继续过下去?或者说,这样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老苏回到贵州老家之后,他的女儿暗示他是最大的罪人,并叫他滚出去,她说,“你是骗子,你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从这里可以看到,老苏与故乡其实是有着深厚的联系的,他出生在贵州,他的家人,包括父母、子女都在贵州,但就是这与他相联系的一切却在不停地排斥他,这样的戏剧性冲突能够让观众更加明白老苏与女儿之间,还有老苏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矛盾关系。
四、表现手法
本片的镜头多运用长镜头,由导演手持拍摄。长镜头的运用就奠定了影片真实性的突出。《二十四号大街》没有让人感觉到一丝认为表演的痕迹,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潘志琪并没有干涉片中的任务,而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静静地抓拍主题人物的言语、动作。中间老苏和琴骑着三轮车到处辗转时,导演就用的长镜头记录下来这些场景,这些长镜头就使得影片更加具有真实感。这些长镜头中的时空有连续性和持续性,不可打断不可更替,这完全符合纪录片对现实挖掘的创作态度,反映着导演直接电影式的冷静、旁观的风格,绝不干预拍摄对象。
除了用长镜头表现真实,潘志琪还运用了在许多人眼中与纪实相对立的蒙太奇用于影片情感表现。蒙太奇可以通过不同镜头的衔接带给观众对于画面叙事的不同理解,不管是在故事片还是纪录片中,导演都需要用镜头间的剪辑拼贴来呈现自己的构想。在公司开发快要被迫迁走,老苏和琴与公司开发人沟通无果,打电话到市委书记黄坤明也没有回音时,导演将将下雪的一幕剪辑到了两人站在棚区画面的后面,冬天一般代表的是一种伤感、无奈、悲凉的氛围,代表着离别,导演用下雪的一幕衬托了老苏与琴两人心中的感伤,暗示着事件已没有回旋的余地,他们又将离开这个地方继续漂泊。后期的剪辑体现了一种导演个人主观色彩的输出,用细节构建着这部纪录片的意义。
影片中的音乐大多也是烘托气氛的纯音乐,并且全程使用同期声,没有一句解说词,遇到必要的场景介绍也只用字幕和图画进行介绍。这也是导演为了保证纪录片的真实性而采取的方法,它需要完全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与场景的转换来表达纪录片的核心思想。因此同期声的优势在于,可以增加影片的真实感和代入感。影片总体上反映着导演潘志琪选择了尊重同期声、反对强加主观解说的创作态度。
五、总结与反思
导演通过七年的跟踪与观察,辗转于城市与农村,拉开了一幅快速经济发展和转型社会下小人物的生存图景。影片聚焦于城乡与小人物生存现状,展现了中国城市变迁的社会语境,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巨大空间变化和人物的变化。
对于影片,导演表示,这部影片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大时代、社会的,一个是小人物的家庭情感。他片子的最后一个镜头,就是想说明这个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有一部分人是没有享受到成果的。这个社会相对来说是公正的,但有一部分人是赶不上时代列车的。在时代的车轮下,个体是无法抗拒他的命运的。观众解读苏永禾的目的,导演拍摄这个片子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更好地去思考: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里,我们如何通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去保证每个个体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权利。
中国三十年的发展我们有目共睹,但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有一些人被丢下了。不只是老苏,还有那些被边缘化的农民工群体,他们为城市发展做出了贡献,又应该去哪里找自己的归宿呢。导演通过《二十四号大街》将沉浸在快速发展与美好未来图景中的观众从美梦中拉扯出来,像是在用尖利的牙齿咬碎一切粉饰,让人直面现实,让观者去了解与理解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真实。
看过这部纪录片,我回想起来我之前看过的另一部陈为军导演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这部纪录片记录着马深义一家对抗艾滋病的一年生活,导演用一样的线性结构按照中国传统节气进行了跟踪拍摄,联系潘志琪导演对于拍摄影片中所展现出来的小人物的苦痛与挣扎,会让人不禁反思,我们该如何用纪录片去真实展现一切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又该如何去保障艾滋病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呢?跟24号大街一样,这两部影片都可能会让人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都让我们直面着现实,甚至《好死不如赖活着》是更加的残酷无情的真实事件。
这类纪实性纪录片,会让我们发现这世界上还会存在这样可怕的一面,但我们可能也会怀疑、追问,它所记录的是否是真实的?然而我们同样会发现,纪录片记录的也只是这个世界的一面,并且它也只是记录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一个事件。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们所看不见的,正在发生着。实际上,纪录片是否呈现真实是自纪录电影诞生以来一直相伴相随的追问。我们现在或许无法完全回答这个问题,但从纪录片的功能来说,纪录片所能做的,正是承担着记录这些事件并将它们留存下来的可能性,让我们慢慢接近这个世界更为真实的一面。对此,导演潘志琪表示:“巴赞在《电影是什么》中提出‘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你想去追寻这种真实,但其实真实跟你永远是条渐近线,与你总保持着一点点距离。而纪录片创作的魅力恰恰在这其中。我刚才提到,一部好的纪录片是作者带领观众在‘界’的边缘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但这个认识是真实吗?其实不一定,它永远都是一个未知数,但在这条渐近线上,你也许会慢慢地靠近它。”对于纪录片中的主观与客观的联系,以及纪录片中是否要有导演主观色彩的介入,导演潘志琪表示:“我纪录事实,首先还是要有态度或观点,或者说自己的立场。你是否能在一个观众看似熟视无睹、充耳不闻的事件中呈现另一个角度,让世人重新去认识一个事件?而,这个角度就是真实吗?不一定。但纪录片导演总是力图在真实的基础上建构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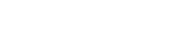






跟着全国的工地逐水草而居的男人,这个经历也是够牛逼的
這是一個名字叫做蘇永禾的民工出軌物語,而不是中國農民工物語。
看的NHK剪辑版 城建主力一瞥 包工头的唏嘘人生 24号大街从下沙大桥下来肯定会穿过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 同样的艰辛 难免想起老一辈曾经亲历的下沙围垦和海塘的传奇
看的我全身起鸡皮疙瘩,因为真实。希望看本片的观众不要站在道德高度去评判任何一个人的人生。每个人生而不易,每一个人都将为自己所做尝得后果。人物命运和社会切面呈现的很好。
有个观点我挺认可,人活着该吃吃该喝喝,开心过好每一天就行
想到宋丹丹的小品,“盲流”,离“流氓”不远了。同样因为生育问题而丢掉公职身份的老苏,在外面开小饭馆谋生,如浮萍般飞翔。回到老家也是家庭矛盾重重,最后的归宿却在争吵中失去,他选择继续出门。一代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史。最后儿子又回到24号大街打工,仿佛如命运的轮回。
最初樂觀隨遇而安依附地盆建築做小生意的流徙族,因應經濟改善城市急速發展而相應的規限越來越多,主角亦開始迷茫失措,富人越來越多城市開始變得沒低收入人士的容身之所,片中帶出很多現今中國的狀況及問題,克制而沒投入自身太多立場在內,作為紀錄片已算相當不錯
以旁观者的角度记录下主角们的人生,请不要用纪录片中的人不是道德楷模来judge片子本身。
3.5 个人觉得这部作品最精彩的地方,首先还是在人物复杂的家庭关系上,这简直是一个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奇观的例子,他本身就非常的纠葛与好看,自具复杂性。其次,才是城乡变迁等社会性话题,在杭州这样的城市里,不同阶层的人在生存现状与价值差异上走向了“超现实的岔路口”。四海为家,回不去的,是那个已没了自己位置的故乡。希望李睿珺、贾樟柯携手看看这部纪录片,找回自己曾经的感觉。#IDF2018
NHK 版。跟不上的拆建
最后一幕十分打动我,主人公两个人在荒野上放了一张床,搭起四面架子,这就是他们的家了,影片就在这里结束了
[2022·浙浪潮]虚伪的欺骗着的人生,漂泊三十几年,一个男人最真实的写照,不讲道理只讲自己内心的自我感动。
被拆,重建,又被拆,回到家乡,也没有容身之处,于是他又回到了城乡结合部,建起了自己的小小违章建筑。p.s.1.老汉有女友还有老婆;2. 中间的撕逼一度以为自己误入真人秀!
【台北金马影展展映】被片名误导了。以为是一条街道的变迁史、众生相。但其实只是关注到老苏一家。感觉素材不是非常充足,即便是关注家庭的视角也有捉襟见肘的单一感。缺乏深度。两星半
杭州的纪录片一直不多,如今其在国内的特殊之处也不是一两部拍得清楚的,混账如老苏,抛妻又弃犊,归乡成殊途,江湖入江湖,搏条活路,聊胜于无。ps维权电话打给市 委 书 记,大型幽默。
长片版比NHK的电视版丰富许多,老苏就是那种“自己长出来“的人物。既不可爱但也不可恨,但绝对像你曾经遇到过的人。
一个抛弃了自己老婆和子女,自己在外和另一个女人流浪打工几十年,终究会身归何处?和农民工还是有很大区别
10块钱的盒饭大多是男人在吃,20的奶茶大多是女人在排队
等长版再看看吧。(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为之的,有一段处理的挺有意思的:挖掘机作业时应该是用了降格镜头,很巧妙的营造出一种定格动画感)
一个城镇化、农民工、拆迁、过日子的纪录片。天道有轮回,宿命的人生,最后导演说片子之后的现实结局还是比较暖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