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惠子从小就有听力障碍,家人为了让她强身健体,送她去拳馆练拳。在训练中,惠子对拳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技艺也愈发精湛,长大后,她在酒店从事清洁工作之余,也偶尔参加拳击比赛。不幸的是,疫情让她所在的拳馆面临经营的危机,作为惠子导师的拳馆馆长也出现了健康问题。在一系列危机中,惠子开始对梦想产生动摇……
海上梦境秋天的童话明日情缘斗破苍穹 第一季你眼中的世界华盛顿广场旅程终点2017紧急营救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绝密押运难以伺候第三季分睡契约安静的乡村女人摇滚学徒死亡地带情定孤堆底逃出玉米地拳脚刑警:唐人街家长指导翻滚吧姐妹成为科斯托2022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潮与虎2015机械特工唯我独尊2022谍血黄埔滩国语版跟踪者的猎物1死亡实验2001雷雨海绵宝宝:营救大冒险(原声)相信奇迹的女孩超能奇才爱的逃兵午夜佩拉宫团子大家族第一季巨兽狂蟒49号旅舍第二季回到明天我甜蜜的胡椒地长篇影评
1 ) 贪婪丑陋《百元之恋》VS和谐秩序《惠子凝视》:日本国民性一体两面
业界有主流观点认为日本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拳击运动大国强国。JBC旗下注册职业拳馆近300家,注册的职业拳手超2500人,其中女子职业拳手可能近500人。

青木拳馆位于东京都新宿区,有超80年历史。因培养出世界拳王木村翔而名声大噪。日本拳馆普遍小型化且训练门槛较低,是日本成为拳击强国的基础。 日本拳击运动历史如此悠久发达折射出日本全盘西化急于融入西方社会的国民精神。

两位年龄相差几乎一代人的导演在此相遇绝非偶然,正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日本电影两个既对立又统一的传承方向:武正晴对今村昌平(1926-2006)的传承VS三宅唱对小津(1903-1963)的传承。 今村昌平以小津助理的身份入行,曾经是小津代表作《麦秋》《东京物语》《早春》的副导演。可他独立执导时却让镜头下表达的日本和导师小津截然相反,被小津骂曰:蛆虫般的日本。今村昌平则认为小津影片中的日本是虚伪的秩序日本。

同样是蝼蚁贪欲之日本,武正晴将今村昌平的揭露批判语言进化为漫画嘲解式。动漫是日本差异化融入西方意识形态的产物,对日本电影业者影响深远。风靡全球的日本漫画不也正是抒发日本国民精神的独门绝技吗?

无配乐,宁静,镜中的面庞眼角带伤,暗示拳手身份。

开篇明确众生相一如今村昌平镜头下挣扎求生的昆虫,但经过漫画式解构。21世纪多元时代,批判不必如半个世纪前尖锐直白,喜剧式讽喻是电影实施批判的最新演变。

惠子咀嚼冰块的声音如此清脆,撩动惠子的无声世界,令人留意影片音效。 两部影片均以女主房间开篇,混乱自困与坚韧恬静对立鲜明。

两部影片还有一个有趣的联系是:1982年生的艺人松浦慎一郎居然同时在两部影片中扮演女主的教练。难道松浦慎一郎本人是资深拳迷?

惠子与教练训练是影片非常重要的叙事场景,反复出现。拳击手套的击打碰撞节拍激荡惠子无声的世界,几乎承担了配乐功能,如同嘻哈打击乐,和弟弟及黑人女友创作嘻哈音乐有互文关系。

穷丑色渣大叔是蝼蚁求生世界的标配。甚至连真实的知名青木拳馆的老板也难免猥琐,与《惠子凝视》中荒川拳馆老板三浦友和是对立的两面。 《百元之恋》的人物设置颇似今村昌平1997年的晚年代表作品《鳗鱼》,又启发了本属于和谐秩序阵营的是枝裕和于2018年推出《小偷家族》,蛆虫的和谐将小津式秩序推向了新境界。

《惠子凝视》标榜的秩序是原生的。


影片和谐秩序下传递出隐喻批判。惠子和斋藤一子在此相遇重叠,都是挣扎求生的弱势女性,一同跻身日本近500名职业女拳手行列,令世界惊叹的日本成就背后隐藏了日本国民性。

2014《百元之恋》。32岁斋藤一子被渣叔强暴夺去贞操才开启自己的拳击训练和爱情,一子的塑造就是今村昌平《日本昆虫记》(1963)《人类学入门》(1966)镜头下忍辱负重求生的女人。《百元之恋》中众多的男人们几乎同样自私胆怯。

而《惠子凝视》极大简化了人物和人物关系,惠子由内而外是如此简单,甚至无一丝爱情的痕迹,编导克制自己的态度的同时也并无意诠释惠子的全部。惠子的情绪被荒川的草木灯火替代了。



1962《秋刀鱼之味》。小津标志性电影语言段落的逗号镜头,被欧美电影学者称为 pillow shot,如同场景转换人物转换叙事转换中的小憩。

多达数十个固定全景空镜和半空镜,占据影片时长近三分之一,是《惠子凝视》最鲜明美学特征,也是对小津pillow shot的心手传承。16毫米胶片,棕金做旧,舒缓淡描了叙事,只留下东京都荒川区远眺人间烟火和宁静中流淌的隅田川。

如此传承和致敬,当然会打动推崇小津的欧洲影人。

具有日本原发性的小津秩序镜头语言和今村昌平欧美技法日本社会学,此两种电影美学方式都得到欧美热捧。 今村昌平式武正晴重叙事的《百元之恋》VS小津式三宅唱弱叙事的《惠子凝视》,不仅承载日本国民性两面一体,也代表了日影两个对立统一的演进方向。
2 ) 旧世界的谢幕与新世代的失语——三宅唱的节律
训练时,一套拳击动作不断重复,我会在第三四遍时跟上主角的节奏,我的耳朵替她听到她制造的碰撞声,进入她身体的律动。这是用节律完成的电影。寂静与爆裂之声的节律;挥洒汗水唾液与血的拳击擂台和洁净的酒店卧室的节律;身体之起伏与城市之吞吐的节律;观众想象主角听不见和观众替主角听见——希区柯克的炸弹爆炸理论反复上演的节律;以及,不同媒介(文字释义手语、照片、直播、日志朗诵)的节律。
馆长的脑血管窄缩,与变迁中的城市无法继续容纳拳馆相互映射;惠子的失聪,与疫情下沟通失效的世界相互映射。旧世界在谢幕,它曾经的必要与荣耀掉入夹缝里,而新的世代尚未找到自己的语言;老者在离场前为新人找到存续之地,而哪里是下一个战场,是否要继续战斗,是新世代自己要解决的问题。
影片反戏剧地以一次胜利的比赛开始,以一次失败的比赛结束。然而,胜利的比赛所带来的伤痛之余震,加以拳馆的变故,动摇了主角是否要坚持拳击的意志。而之后豁出全力却惨烈的战败,引向的是另一次自我识别。影片结尾处导演安排主角偶遇自己对手,这擂台上另一个相当爆裂的灵魂此刻身着建筑工人的灰色制服与头盔。至此我们耳边都会响起主角的话「拳击让我释放工作的压力」。这些无声地维持着城市的建设和运转的生命,在拳击台上找到了另一种存在证明;拳击台为这些「底层」生命提供了另一种节拍。而女主恍然大悟似的眼泪究竟是来自一种同类相认的感动还是发现这残酷真相的自嘲?我不得而知。在堤坝的剪影上她开始奔跑,就像馆长在收看她战败的直播之后突然自己转起了轮椅,向未知之处前往。只有这是我们可以掌握的:我们的身体,和它前进的速率。
3 ) 【自译】三宅唱采访:想要拍摄到无法命名的“特别瞬间”
——我特别被女主角岸井雪乃的背部和肩膀所吸引。在拍摄演员的身体时,您有什么看重的东西吗?
三宅:演员各有自己的表演思维与对身体使用的方式,虽然与运动员所拥有的运动神经不同,演员需要用自己的身体来工作,这完全是他/她一个人的工作,不知不觉中也有吸引人的东西在,举着胳膊,稍微向右偏移一点,就会让我看到世界突然起变化的瞬间。这次岸井真的是以非常棒的集中力出演的,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将纯粹的身体动作拍摄下来。
——听说导演在三个月的准备中还和岸井一起打过拳击。在这之前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是导演您自己的意愿吗?
三宅:是的,那是我的意愿,在一开始我并不是个拳击迷,但是我认为像我这样不懂拳击的人站在镜头后喊OK或NG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首先想动动身体一起学习,第一步是一起练习。现在我把它当作一件纯粹的乐事。
——这是一个在小笠原恵子《不要输》的小说基础上改编的剧本,并诞生了名为小川惠子的新角色。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有容易理解的困难与契机,故事发展也并非曲折,对您来说电影中的“故事”有多重要?
三宅:当我开始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的想法发生了很多变化。说实话,当我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我对故事并没有太大的兴趣。相比电影,小说、漫画在讲述故事时更胜一筹,更洗练且传达很多东西,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里,我固执地认为摄影机可以捕捉到的不仅仅是故事,但是,我一直很喜欢看美国电影和经典电影,当我看得越来越多之后,渐渐意识到正是因为这些“故事”使演员和场所发生了变化,同样的故事由不同的演员来拍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为了让某个演员或某个场所发挥出他们的魅力,需要有合适的故事,这是一部电影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你说你提前做了两部参考视频,包括茂瑙的《都市女郎》中的火车场景和拉斯·冯·提尔《黑暗中的舞者》,这是为了什么呢?
三宅:总之我们的出发点是拍一部新的拳击电影,虽然大家已经把这样的想法当作共识,都说“噢,明白明白”,但这毕竟是专业性的东西,我想如果没有某种更具体的东西的话,先不说创新,能不能描绘好现有的都是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制作一个参考视频,更具体地分享出我想做的工作。这个办法我是第一次尝试,但效果立竿见影,是一个不错的方法。除了你刚才提到的电影,我还剪辑其他几部电影,这只是给工作人员看的,做得比较粗糙,除非我在旁边解释,否则你看不懂。
——那影片中哪些镜头是这样拍成的呢?
三宅:举个例子,电影刚开始大约五分钟。有一个场景是惠子和她的教练做组合拳击练习,大概很容易被拍成让观众一起走上拳击场的感觉,好像正在通过拳击手以逼真的摄影技术拍摄的,这是在各种各样的拳击电影中被使用的手法,但我们并不是这样做的,我们将摄影机放在拳击场围栏之外(机位是固定的,不会移动),在一系列固定机位的画面中捕捉整场动作画面,这就是我从文森特《篷车队》(The band wagon)中的舞蹈场面学到的,我们大家都觉得这样做很有趣。
——它主要由固定镜头组成。
三宅:是的,几乎固定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三宅:首先,在拳击场景中身体本身有很多运动动作,而对拳击手而言,其内心的感情和想法是很难表现出来的,即使心里有非常大的起伏,反映在表情或身体动作上也只是一个微妙的变化,在这时如果摄影机跟着移动,可能就看不出这样的变化了。因为被摄体本身已经像水一样、小波浪一样在移动着,所以需要我们去凝视它,必须是固定的,这一点我和摄影师月永雄太已经达成共识,即用固定的摄影机捕捉移动的东西。
——在拍摄前你做好了削减预算的准备吗?因为要看作品的实际完成情况的话。
三宅:这次是用16mm胶片拍摄,能用的胶片数量有限,所以多少提前做了计划。不过并不是计划了全部细节,而是想好了所谓的主镜头(master shot)的表现,剩下的再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灵活应对了。
——滨口龙介会为演员提前准备好一些潜台词,那么您会为演员提前做什么准备呢?哪些针对演员的准备工作是您比较看重的?
三宅:我认为这取决于演员在电影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在戏中占多少分量,与其说是事先,不如说是在进入拍摄现场后我们会谈很多。接着在进入拍戏状态时,大家都表现出认真样子,并对眼前发生的事物产生出非常强烈的反应,这与戏外的状态会有极其微小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在我看来很重要。
我们的身体存在于对各种事物的反应中,远处鸣响的电车声、光线、温度什么的,正是因为有了对它们的感受才有了身体的存在。但是在面对镜头时,有时会刻意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在我的电影中,是可以对各种事物做出反应的,随时抬头去看一只正在唱歌的鸟,对刺眼的光作出反应,觉得吵的话就大声说话,觉得安静的话就压低声音,等等。我希望演员们可以对整个环境而非限于表演对手开放他们的物理传感器。我可能说得有点粗糙,但这就是我的想法。
——我之前看过导演关于这部电影的采访,对电车的那个场面十分期待来着,而实际呈现的效果更是超乎我的想象,高架下的那个场景太神奇了,那场戏是怎么拍的呢?
三宅:在拍摄前,我和制作部的大川和城内一起在荒川周围走了很多路,与其说是在寻找地点,不如说是在散步。在了解这个城市时我们也一边聊着电影,“不知道如果惠子在这里会怎么想,她的心情会怎样,会怎么看?”我会带着这样的想法去观察周围事物,全副身心地度过那段散步时间。有一次,我发现,“当我们在这座桥下时,我们通过桥上的轰鸣声知道有火车经过,但惠子一定是通过这里的灯光反射知道火车的交通情况”,我说,“我们就来拍这个吧。”然后我们找了个好地方在那桥梁下走,摄影部和灯光部都去看了,还有时间准备,比如看看火车漏出的光到底会不会反射到电影上。但我认为一开始重要的是,我能够用自己的身体在这里走动,发现各种事情。
——我想问一下您是如何制作这种灯光的?
三宅:当然,当然。其实火车本身并没有出现在镜头里。照明部门准备了一个特殊的装置,类似于一个旋转的银色圆盘,当圆盘转圈时用灯光去照射,就会产生如同火车驶过的光影。我的解释有点粗糙,不知道你明白没有。
——你在之前的采访中说过,如果每次都拍脸部的特写镜头,就会得到一些无趣的东西。这次影片中的特写镜头非常少,但是还是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惠子的存在,你是如何决定什么时候给特写什么时候不给特写的?
三宅:唔,如果我真有这么个完整的规则,那我的工作就简单多了,其实每次拍摄时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情况出现。 我在拍《惠子》时发现,拍戏时是有真事发生的那种巧事出现,例如在拍与社长的对手戏时,如果社长真的就在你面前,就会出现现实生活中那样的反应,那样就很好拍了。
不过大多情况只能根据剧本来提前想象,例如,惠子收到拳击社要关门的短信,如果她是真的第一次知道,就可以捕捉到一个惊讶的表情反应,但其实这一幕早在剧本里写好,所以在拍摄时你只能去表演这样的表情。不过我想如果是岸井的话,她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她能令人信服地创造出拳击社关闭时那个使人震惊的时刻。 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同意这样做,或者其他什么。我不知道,这是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这是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好吧,我不能判断它是否可以,所以我想我拍那些东西的方式,嘛,我还想过用不同的镜头来拍全身的反应这样的方式呢。对不起,那是一个有点奇怪的例子。但总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事情的发生是真的还是假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演员的表演。
(三宅唱的脑回路和语言组织……怪不得他要自制个剪辑视频才能表达出自己的需求……)
——这就是三宅先生所说的“一次性”吗?
三宅:啊,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就是这样的感觉。我认为即使是最好的演员,在对同一件事表演多次后也一定会产生变化。 但这次与岸井合作时,我们的第一次交谈让我觉得有点惊讶。她说:"不,我认为提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再表演会更安全,这样我就可以把它放在'一次性'的基础上,不用担心"。 因此,为了得到 "一次性"的效果,我们实际上做了很多测试,甚至在实际表演之前,我们做了所谓的 "真实测试",就像实际表演一样,即使只有摄像机但没有转动,我们也进入了实际表演。 我觉得(岸井和其他演员)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 "本色 "层面,与我作为一个业余演员所认为的 "本色 "完全不同。 我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同的,但仍...
——在我不是很了解镜头的情况下问你这个问题有点难为情,但我想,你认为镜头是与“叙事”相反的东西,或者说是对它的扩展。不是说为了顺利地、没有违和感地拍摄,而是一种超越“叙事”的瞬间和时间的感觉?
三宅:哦,是的。是在抵抗些什么,换个说法,我在与“叙事”做斗争。关于某个场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先入为主的假设和偏见都可以在片场变成现实,或者,如果你改变角度。以某种方式引导,那么就可以表现出“噢,实际上这一刻也可以是这样啊”的感觉,例如,表白被拒的时刻,好吧,那种确实会有千差万别的场景,那如果说是一个人的现任与前任见面的场景,大多数人可能会想,"哇,这太尴尬了",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场面,我想你肯定会觉得很尴尬,但在片场里,你现在的爱人和你以前的爱人可能会一拍即合,也许在那一刻你超越了所谓的爱人或前爱人的角色,或者其他你被赋予的任何属性或标签,一种新的关系会诞生。在这个意义上,“叙事”转变并动摇了这些形象、偏见、成见和标签。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一部电影就可以很有悬念,很刺激,如果你去追求那种画面,那种场景,那种人,那种东西,我觉得有点无聊。 如果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是这样的......是的。
——我不认为过多谈论这部电影是个好主意,因为这是你必须留给看过这部电影的人的事情,但在《惠子》这部电影里有很多这样得感觉,在这些场景中,你有什么可以表达的吗?这是一个粗略的问题,所以觉得不好回答也没关系。
三宅:噢,不不。电影本身是关于当你把 "听不清的拳击手 "或 "女拳击手"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时,你会想到的形象,以及它不是,或者它看起来像什么,以及你认为那里的偏见和成见,我们懒得去推翻它们。 例如,我喜欢这部电影的一个很小的地方是,当惠子和她的哥哥在入口处经过对方时,他们有一个小小的手语交流,弟弟说:"我现在要和我的女朋友去看电影,你也想去吗,姐姐?" 那一刻她脸上的表情可能是一个很短的镜头,因为只用了一瞬间,但它显示了惠子的一个新鲜的方面。 我想这是我能够捕捉到惠子的这一面的时刻。
——是温柔的笑容。
三宅:对的。
——三宅先生拍摄的电影类型非常广泛,包括现代剧,如《惠子,凝视》和《你的鸟儿会唱歌》,时代剧《密使和看守人》,恐怖剧《咒怨之始》,有大量纪录片元素的《野性之旅》等等。 在制作跨类型的电影时,你会有意识地改变什么,又会有意识地不改变什么?
三宅:基本上,我每次都会尝试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在我目前所做的工作中,我试图反思以前的工作,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以前的工作(这只是在我心中,而不是在评价方面)。我认为,因为我以前做过这个,但这不是表达一部电影的唯一方法,那么下一次我就尝试不同的方法。我每次拍电影都会尝试做一些不同的事情。这与其说是一种流派,不如说是一种对电影本身的思考方式。然而,我后来发现,尽管我尝试了又尝试,电影中的相同部分还是没有变化。我想这更多的是后来发现的东西,而不是事先发现的。类型的选择真的是偶然发生的,因为我很幸运地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这并不是我在选择它,我没有意识到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但人们会对我说,"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有时他们会说,"你应该缩小范围",但我会说,"不,等待,等待"。 我认为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总是不同的类型,美国电影导演都是不同的类型,所以每次......嗯,有人说恐怖就是恐怖,但我认为类型变化挺大的,所以我不打算改变,如果有一个有趣的主题,我会拍一部关于它的电影。如果有一个有趣的主题,不管是什么类型,我认为我的工作是为这个主题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法。
——你刚刚说的“后来才发现没有改变”指的是什么?
三宅:例如,我认为有些关系是有名字的,比如家人、兄弟姐妹、同事等等。 我感兴趣的是那些没有名字的关系。从最好的朋友到普通的熟人,定义因人而异。不同的人感情持续的时间长短不同,每个朋友获得的幸福程度,我觉得也是完全不同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麽,粗略地说,如果摄影机能捕捉到这些关系中一些无法命名、还没有名字的快乐时刻,那就更好了。
在《你的鸟儿会唱歌》中,把恋爱排在首位的话就是朋友以上、恋爱未满那样的感觉,但恋爱并非总是排在首位,他们三人之间并没有这样的上下关系之称,它是只存在于他们之间的一种东西,暂且把它叫做友谊或三角恋好了,但肯定不是通常所说的油腻关系,而是一种难以言状的时刻,这是我的电影想要捕捉的。
《惠子,凝视》的话,则类似是一种师徒关系,或者是在拳击社里的伙伴和教练的关系,与爱情、家庭都不同,它们展示了在同一个健身房里碰巧相遇的不同人之间的幸福时刻。我想我已经能够在一些电影中捕捉到这一点,所以我最近意识到这些东西是所有电影的共同点。
——听到这话,我突然想起在《惠子》里,松浦在练习时突然退出过一次,然后又出来了……
三宅:是的,他是去哭了。
——当时岸井的笑容也很灿烂,我在想是不是那样的一个瞬间……
三宅:嗯,是的。之后松浦先生哭著出来了,惠子笑著迎接他。由三浦诚己和柴田贵仔扮演的见习拳击手,只是在旁边看着他们,然后和他们一起练习拳击步法,模仿他们在擂台上看到的情况。我实际上无法在剧本中写下那一刻,我就是不能,但我希望有这样的时刻,在拍摄现场相当困难,但这是我很高兴能够捕捉到的那些时刻之一。
原文链接: 三宅唱さんインタビュー「名づけえない“特別な瞬間”を撮りたい」 | NHK北海道
(节选翻译,日语小白,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4 ) 《惠子,凝视》:一起凝视吧
不只是失聪的惠子在凝视,我们同样在凝视。 会长说过,惠子并不算是有天赋,但是她视力很好,善于观察对手。 摄影机同样带我们去观察去凝视。 业余学拳击。配合默契的拳击训练场面,惠子反应迅速,熟练出拳,见出专业拳击手的素质。 工作是酒店客房服务员。惠子整理房间,擦洗,刷马桶,一丝不苟,是另一种专业。 通过一系列的生活化场景的展示,我们在凝视惠子,了解这个人。会长说,她虽没有天赋,但有诚实勤勉的品质。 所以就这样脚踏实地的,带着有些残疾的身体,做着一些常人难以企及的事。 本片其实还是励志片。疫情下人们生活艰难,电影可以给一些安慰,给一些方向。那就是像惠子这样勇敢地生活下去。 拳击馆十分老旧,疫情期间终于无法支撑。会长也被疾病侵袭。片中的人们,工作都是服务员,保安,厨师一类的底层,但他们都有各自安放心灵的地方。惠子找到拳击,弟弟喜爱音乐,做保安的师父教拳击。对于经济低迷多年,生活似乎看不到亮光的人们来说,本片似乎可以给人一些力量,如片尾惠子的那声呐喊。 与一般的励志片不同,主人公的获胜不在最后的比赛,反而在前半部,最后却以失败告终。但我们看到,胜利和失败的意义与我们惯常理解的绝不相同,胜利后的迷茫,失败后的坚定,是一种成长。这是本片极为独特之处,也让我们不要以成败论英雄,改变看待事物的方式。片尾,获胜对手向惠子道谢,看着这位同样在底层工作的女子,惠子的表情有些复杂,她一定感悟到了什么。 还是那句话,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中的收获与感悟。 本片迷人之处,在于展示真实的生活,而毫不令人厌倦。日复一日的日常,人们做一些事,说一些话,有时颓唐,有时喜悦。 失聪拳击手有很多谜团,吸引我们走进她的生活。弟弟问她为何喜欢拳击,她说喜欢出拳的感觉。很多事就是这么简单,朴实无华。对着生活出拳,是一种不放弃的姿态。 真实的生活很动人,城市的噪声,清脆的鸟鸣,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发生,当通过摄影机去凝视这一切,平凡的生活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惠子走过列车呼啸而过的桥下,那闪动的光影,让人一时分不清车里车外,梦幻还是现实,生活中需要这样升华的片刻,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存在。不如,就这样凝视。
5 ) 比《车》更像村上哎
8.5
很动容的一部电影 截取了一个很小的故事接口 认真且细腻的讲叙了关于惠子的拳击生涯.
将故事设在了疫情背景 同时主人公是一位听障人士无疑反应出了一些有关于疫情时代的话题.口罩把嘴唇与视线阻隔开来 正是切断了惠子读懂他人的通道 这种沟通上的障碍 也恰恰是疫情时代 人与人之间无法深入沟通的真实写照.我们在疫情时代沟通障碍的焦躁与无助 也正是通过惠子展现出来的.这才有了“我对你很失望”的误解.
另一方面视听语言也很有魅力 影片开始 导演通过声音的分离叠加 逐步的把我们带到了故事当中 这种渐入性 比一个空镜头更具有电影感.影片中通过惠子母亲拍摄的照片 我们可以强烈的感受到惠子母亲的紧张情绪 无需配乐 无需表演 仅仅是照片的播放 变可以达到如此的效果 实在这让我很惊喜.后半段惠子的日记 没有什么升华主题的金句 只是不断重复的训练内容 可生活不就是如此吗 反复却有力量 .对于手语的字幕翻译 当惠子生弟弟气的时候 字幕是在画面后面的黑屏上展现的 如同两人之间间隔的心理距离.导演对于情绪表达直接给出肢体语言的特写也很见功底.
影片A线讲的是惠子 B线说的却是疫情.这不像《中国医生》一样直击疫情中心 而是将其放在了背景里 一个柔和的残酷的空间下 去讲述关于个人的事. 但是又不仅仅是疫情 期间夹杂着一些对于生命的无常 对于理想与生活的思考 有些杂 似乎也没有答案 可生活也本没有答案呀.
不过影片对于惠子理想的动摇展现并不充分.影片展现的也并不是太多 对于疫情 对于理想与现实 对于生命等等.
6 ) 别认输
1
影片开头,还在黑屏的时候,就传来“沙沙沙”的画外音。
那是惠子在写一封信。
这封信,一如她的生活,她写得很痛苦,很艰难。
2
惠子是一个普通,但又不普通的女孩。
说她普通,是因为她和你我一样,不过是这喧嚣的都市里,滚滚人流中的一员。扔在人堆里根本就找不出来。
长相平凡,工作平凡,生活平凡。
说她不普通,是因为她从小就丧失了听力,是一个聋哑人。
因为沟通不便,她很少跟人说话。不得不说的时候,她会用手语,或者通过写字来跟人交流。
惠子来自乡下,独自一人在大城市打拼,或者说,生活。
其实这两个词用哪个都可以,因为对她来说,生活就是打拼,打拼就是生活。
平时,惠子是一个普通的酒店服务员,收拾床垫,打扫卫生,清洁马桶,做事认真而负责。
工作之余,她是一个专业的拳击手。
每天早起,热身,郊外跑步10公里,换衣服出门,工作,换衣服下班,到拳击馆训练,回家,睡觉。
村上春树说过,拳击手跟拳击互相吸引,就在于那是一项沉默寡言的运动。
拳击的时候,你不需要多说话,甚至不需要说话。你只需要挥拳就可以。
惠子那么喜欢拳击,这或许是原因之一。
此外,在别人问起的时候,她自己也说过,拳击能帮她发泄身上的压力,而且挥拳的感觉很好。
这就是惠子的工作和生活,沉默,简单,充实。
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这种状态会一直继续下去的吧。
直到新冠疫情降临,直到拳击馆即将倒闭。
3
惠子是一个聋哑人,本来就很少说话。
疫情降临之后,人们都戴上了口罩,互相的交流变得更少。
她失语了。
但是,失语的只是惠子吗?
不。失语的,更是疫情下,每一个平凡的我们。
整部影片中,惠子真正开口说过话的,只有两次。
一次是拳击馆因为疫情即将倒闭,会长见她情绪低落,跟她说拳击这项运动,没有战斗的意志是无法做到的。问她还要继续打吗?
另一次是会长病危入院,会长的妻子私下鼓励惠子说,让她别担心,大家都很期待她接下来的比赛,让她继续努力。
两次,惠子都轻声却坚定地张开嘴,用日语回答:嗨。
4
没有含着热泪挥过拳的,就不是真正的拳手。
对手很强,压力很大,训练很苦。即便如此,还要战斗吗?
坚持很难,放弃一定很容易吧。即便如此,还要战斗吗?
生活从来就不公平。即便如此,还要战斗吗?
跟命运战斗,也许偶尔能赢,但迟早会输,注定会输。即便如此,还要战斗吗?
……
这部影片改编自小笠原惠子的一本小说,名字就叫——《别认输》。
5
影片结束,画面切换到这个城市。
有的是地铁,有的是河边,有的是公园,有的是街道,有的是立交桥,有的是十字路口。
在这些地方,喧嚣嘈杂,车流滚滚,人们往来如常。
随着银幕变黑,影片结束。
这时,一个画外音渐渐响了起来。
淡淡的,轻轻的,却每一声都打在我的心坎上。
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深夜。黑暗之中,听到这个声音时,我差点滚下泪来。
这个声音是什么,我就不剧透了。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你也会听到的。
6
这部电影的中文名叫《惠子,凝视》。
它被日本电影旬报评选为2023年度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
我个人觉得实至名归。
疫情刚刚结束,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好电影。
影片的英文名我也喜欢,它叫做《Small, Slow, But steady.》
微小,缓慢,但坚定。
真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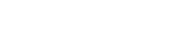





















任何热爱以(视觉和文本双重意义上的)“奇观”来制造所谓“戏剧性”的作者都应该来学习一下,怎样用影像的表现力去达成叙事层面的起承转合、人物情绪的跌宕起伏,言语的文本被消融到镜头诉诸的意义(以惠子与他人互动的几个桥段就勾勒出所处的环境和人物基本信息/性格),日常的静水流深被拍得余韵十足。从开场的练拳节奏即敲出本片独有的节奏——蓬勃而沉静,寂寥却有力,电车驶过的市井隆隆声,是无法直接沟通或倾听的人类孤独之声,然而也蕴含了每个清早醒来渴望为自己寻到努力奔跑的强劲脉搏律动,人物和影片本身获得了一致的节奏;在与惠子共同凝视的静谧中,我们看到更辽阔的世界。喜欢暮色街头的背影,拍糊的比赛照片,结尾逆光中的仰拍,以及拒绝来之不易的下一家拳馆机会。
#72ndBerlinaleEncounters 平缓的、轻盈的、孤独的,故事发生在当下,又像很久以前。
精确且内敛的无声孤独
虚伪且没有意义。
柏林電影節。這是另一種型態下的東京,沒了燈紅酒綠,沒了繁華喧囂,甚至拍到遠景時,整個畫面都是灰藍色的。但就是這樣不溫不火的東京,才會讓我甚是想念。
4.5。影片的色调控制的极佳,不动声色中契合了人物那在冬夜里逐渐熄灭却又在不断迸发最后星火的内心。这片回答很多用言语无力表述的问题,比如为什么看电影:我厌倦了看一个惊心动魄的戏剧性故事,或者情深意切的表达某个理直气壮的观点,或者自诩为百分之百的现实还原,或者处心积虑的煽动奇观。我只想看一个我不认识但却渴望了解的人物或者环境和他们/它们内在的闭环真实,其他的都请从影像中退却。《惠子,凝视》和三宅唱的其他片子,都跳过了那些累赘的媒介而直指这个核心。
“去热血化”在现有的体育题材影片中也早已不新鲜了,何况这样的本子放眼全球也有过太多了吧,只是人物的职业背景不同,但同义替换总是奏效的,主题是共有的。我是真心不懂为什么国内在吹这位导演…
我们之所以能在这个对每个人都均等地赋予繁杂与宁静的城市中发现惠子,注视到惠子的身影,是因为她的比赛在拳击台之前就已经发生(高潮的重心不是惠子的比赛,而是注视正在比赛的惠子的“眼睛们”)。惠子在这片散落于远景镜头的城市的人群中,并非她成为了镜头的焦点,而是与城市的比赛中,不正对镜头的她眼中总有着坚定的前方,一如拳击台上的孤独个体。五十年前,寺山修司写下拳击台的彷徨之言:“明日必定有什么东西存在,但明日在何方?”当下,惠子的感官没有了耳朵,我们的容颜没有了嘴巴,但幸好我们都拥有眼睛,那个连接彼此通往明日、开启二十年代之现代关系可能性的共同器官。
惠子让我看到 打拳击可以不出于任何noble cause 不用像百元之恋需要一个爆发力强劲的腰腹力量来掌控我的生活 不需要啊荒野一样为了与人相连 我做这件事可以只是因为punch感觉很好 我所做让我赢的是“起床 出门训练 工作 睡觉” 没有那么多戏剧 没有那么多惊喜 当片中出现唯一一个可能是与惠子compatible的男性角色 而他在中途离开了 我就知道这不是普通带有强烈故事性的电影 我的生活 可以无趣孤独三点一线不被赋予伟大意义平淡卑微 但生活中的微弱细节还是让我感受到温度 不是符号学意义上的 而是真正人与人之间让你平静又拉你一把的东西 我或努力或放松过着我的生活 而活着这件事本身已经可以成为史诗/年度十佳之四
想引用三句话:1.布列松:正因为有声才能听到无声。2.塞克:Motion is emotion。3李小龙:不要去思考,去感受。
就像村上写道的主人公,惠子与拳击之间的互相吸引,就在于那是一项沉默寡言的运动(电影里也有类似台词)。无论是在陈年历史训练馆里,枯燥、单调、重复又有挥汗热血的撞击暴打声(首尾各有一场几分钟的固定长镜头),还是没有任何铺垫、直接出现的拳击场比赛较量,《惠子,看好了》都是一部安静,却充满跳动于体内的各种声响,日复一日小心翼翼去量测生活深度的电影。正如,也许惠子在紧张训练的余裕,喜欢在河岸放松,还有路道上出现的洪水季最高水位线标识,都不是偶然。拳击在《惠子,看好了》,变成了听障群体日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那些一下子看不到,被正常人所忽略的“人生深度”。三宅唱恰好就是一位擅长在日常里寻找韵律、节拍和美感的导演,而无论是比赛,还是人生,你总有一天会被打败的。作为观众,是有没有能力,去理解深度这东西的存在
三星半。丧燃的日影永远比那些top250式糖水片更深刻也更治愈的一个原因:糖水片不必看前面多惨,最后一仗一定能赢,从此主角迎来新的人生。但我们分明知道,凡尘俗世,没有那么多大舞台的关键战役,我们更没有一定能赢下来的运气。比赛输了、武馆关了、会长老了、梦破灭了,人生还能过下去。武馆老板娘陪轮椅上的会长看完决战视频,合上平板,说,肚子有点饿了。输掉比赛的惠子如常打工,教后辈如何掖好被角,迎着夕光跑上河堤。不是英雄的我们,需要这样释怀的时刻,回到喧嚣市声与孤寂内心中,继续生活。无法通感听障的世界,但总能共情孤独与韧劲。不满在三宅唱还是过于匠气,才气不多,全片都没有灵光一现的惊喜。旬报最佳未免过誉,但健听女孩都能捞座小金人,那旬报十佳含金量还是远高于当下奥斯卡的。
沈靜細膩而內斂,拳擊成了自己在疫情當下 在城市中保持生活節奏和寄託的方式,是每天克服與其他陌生人細微的溝通障礙後,能繼續安靜寫下日記內容的堅持。當惠子的日記內容就這麼重複著每一日的訓練,但有次平靜享受,成為她的生活寄託時,那種日復一日累積的力量,瞬間讓我淚目。導演能捕捉這個城市被人忽視的角落,每一處光影,每一種律動,每一種平凡生活。結尾台上對手在日常中以另一個身分跟她打招呼,互相鼓勵時,我不過一個酒店清潔員,你不過一個地盤女工。讓我想我drive my car中反覆引用萬尼亞舅舅裡的那句話,要活下去,要度過無數個漫長的白天與黑夜,活下去。感謝導演,對疫情時代的普通你我無聲而溫暖的慰藉。
一部主角是听障人的电影,却让我们聆听城市的声景;一部关于运动的电影,却让我们留意生活中的慢、弱与静;一部疫情时代非常当下制作的电影,却用影像的质地带人回到上世纪。
胶片拍出来了这个片子底层的气质, 没有热血,没有英雄。是千篇一律几点一线的生活。拳击是惠子凝视自己凝视生活的洞。在所有人都期待惠子能赢的时候,她输了。输才是对的,普通人的生活哪有那么多戏剧性的转折啊。当惠子站在河堤上遇到了赢她的对手,发现原来对方也是一个和她一样的普通人,瞬间释然了。只不过是赢了一次,只不过是输了一次。 珍贵的是拳击馆的日常,是和弟弟还有弟弟女友打拳时突然跳舞,是给指甲涂点颜色,是拳击馆老板送的帽子,是站在河边感受到莫名的痛苦,是有人无意识的救了你,然后又离开了。
惠子不是真人的化身,三宅唱與岸井雪乃合力創作了一位,投射我們在疫情時的困境與局限的角色,她在日常生活中的遲鈍與無法察覺,日常聲音震動,唯有專注眼前,只有當下的狀態,身體的缺陷更成為當下我們的缺陷,我們可曾如此寂靜地面對過自己?「沒有人不怕痛,但拳擊讓我感覺到自己。」正拳擊和聾啞放大了身體感,三宅唱捕捉了在疫情時期的身體節奏,用一種具有觸摸能力的視覺與聲音設置,記錄下事實,沒有背景音樂,但有豐富細緻的聲音表現,超越敘述性的描述,是非理性的,非智力性的,深深地走入我們的身體,如果德勒茲說法是對的,那三宅唱同樣可以在一種色彩、一種味道、一種觸覺、一種氣味、一種聲音、一種重量之間,應該有一種存在意義上的交流,從而構成感覺的情感時刻。讓觀眾與銀幕共震,達到連結的可能。
4.5 从未如此静谧的东京,依旧微妙动人的三宅
核心表达是,拳击运动作为一种个体生命特殊又普遍自然化之存在方式,全然跳脱于成功励志学之外。三宅唱最挥洒从容之处是,在一片片暖意的晕黄灯照下,能异常流畅地把握住生命挥洒的节奏能动感,通透有风致,这不是简单地去戏剧化就能轻松做到的,绝对不能忽视一个状态连缀一个状态的结构是如何自然构建起来的。那些羸弱悲苦个体存在于世间之崇高之残忍的情境,惊天动地又寂天寞地,让人唏嘘怅惘又觉自是如此。值得起立鼓掌三分钟的大师级作品。
安静而有力。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赛场和拳馆,而是工作的那个小酒店,刷着马桶,掖着床单,以及惠子的对手穿着脏兮兮的工服过来问好。她们带着在赛场上获得的明显的伤痕回到日常生活,又带着生活里、工作上带来的看不见的伤痕返回拳馆。或许只有下了班坚持去训练的人们才能从这电影里体会到切身的一层意思。某种超越性的抵抗,一种接受俗常但绝没有被俗常化掉的抵抗,安静地抵抗,没有表演性的抵抗。
直至影片最后一刻,当获胜者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出现在失败者的面前时,我们才明白,无论在赛场中多么激烈,回归生活后仍要被庸碌的人生所支配。赛场是理想、是寄托、是宣泄地,是自己选择的游戏。而生活只有生存一个主题。愿望中的世界很美好,但终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泰森、阿里。她是酒店后勤,她是建筑女工。在这里没有胜者、败者,只有贫穷与富裕,孤独与自洽。喧杂的城市背景音,裹挟着人们不断向前行。人们心中有火,却渐渐被生活浇熄。还会有更多年轻的面孔络续登上拳击台,而还有更多的人最终只能被淹没于生活的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