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南方某小城里,年轻少妇周玉纹和丈夫戴礼言的夫妻生活淡而无味,两人已经几乎没有什么言语上的交流,周玉纹只是仍恪守着做妻子的责任。周玉纹喜欢时常到城墙上走走,有时能在那里呆上一整天,但没有人知道她在看什么,想什么。戴礼言长期抱病,终日郁郁寡欢,他对家道的日益没落感到无可奈何,而对妻子的疏远无法接受却又难有作为。陌陌影视陌陌影视樱花影院6080影院飘零双燕钢琴之森海底大揭秘:二战船舰冤罪律师地球改变之年青春摇滚火花今天少主不在家飙速宅男糊涂好孕姐 第一季名门绅士2:淑女之心之三东方商人迷镜请告诉我去车站的路逃脱2012爱莎强尼大战安珀苏乞儿(1993)睡美人2016一叶小舟放逐之徒天使2013失踪的女人我的X一样的20岁乘风破浪2021脂粉双雄世界大战2:新的进攻安妮 第一季初到香港美国犯罪故事 第一季
长篇影评
1 ) 田壮壮版《小城之春》的几个构图元素
不说费穆版《小城之春》,都知道它的特色独白,它的百无聊赖,它的欲语还休,还有它的那种文人式的抒情结构。田壮壮想必是胆大包天,否则翻拍经典本身即包含了无数未与风险。新版摈弃独白的做法至今褒贬不一,我不作评判,但我敢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费穆版本的先入为主,新版小城之春一定是部杰作。
下面主要从构图方面简要说说田壮壮版是如何堪称杰作的。
第一是深巷灰白乌黑的断壁残垣。新版不是黑白片,说断臂是战争遗留下的印记固然不假,但和鲜艳精致的人物装束比较起来显然搭不上调调,毁坏的墙壁如果没有特殊涵义,摄影机也不会一而再再二三地穿过崩塌的墙壁拍摄缓步行走的玉纹。这种特殊含义就是环境对人的禁锢。深墙大院里会有一只红杏出墙来,小家碧玉无拘无束反倒很不容易越墙而绽,原因很简单,因为压根没有院墙的阻拦。同时这个出场的造型也给故事结尾埋下了伏笔,不止是外遇,婚姻,爱情,人生往往也都如此,当自由得没有限制,自由本身也就成了限制。
第二看看城墙。玉纹是自由的,她很可以“为所欲为”,但她却每天一尘不变地挎着篮子去到蒿草衰黄的残破城墙,在那踱步远眺。不妨作个小小的语义符号的转化:长满茅草的城墙可以看作女性不能满足的肉体官能,爱情不是情爱,嫁给病歪歪的礼言连身在曹营的满足都没有,但又没办法冲破传统和道德,于是只能挎着那只象征着传统和责任的篮子,怀揣着遐想,“意淫式”的远眺,企望某一天还能得到满足。
她也试图做过一些尝试,最激烈的一次是在戴秀16岁生日的晚上,或许是醉酒的志忱勾起了她压抑的爱恋,或许是受不了志忱那醉人的情歌诱惑,但不是有戴秀在画面中间的割裂(又一个重要构图,生日那晚,两个人就没有同处一个画面过,要么是一群人,要么是中间隔着戴秀),就是酒醒时志忱心怀亏欠,最后一步终未迈出去,最终二人不欢而散。
第三看修剪的树枝。春天将至,万树萌芽,自志忱来时院里就有不少粉红桃花绽放,但最后一幕却是礼言在为一颗尚未发芽的树修枝剪杈,自然不是时光倒流,只是故意拍摄了这样一个场景。也不妨做个假设:本想结束生命的礼言,起死回生,也深切感受到了玉纹对他的爱,借修剪还没开花的树干实际上在暗指礼言终于可以打理打理他无处释放的利比多。单凭这点可能还不够,再看手绢这个造型可能更为明显。
玉纹除买菜溜城墙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绣花上,不知道她的手绢是不是自己绣的,第一次出现手绢是玉纹与志忱在城墙散步,玉纹告诉志忱那颗树上的手绢是她的,于是志忱爬上去拿到手绢,向着玉纹挥舞,玉纹显得很兴奋。对这部分做个转换就是玉纹随时有夫之妇,但对志忱一直不能忘怀,手绢正是志忱心意的表征,坐于家中绣花是女红的束缚,送人手绢才是心牵的爱恋。一个很小的细节是结尾当礼言在修剪树枝时,玉纹掏出手绢为他擦汗,这分明是心意的转移,至于转移是出于责任,还是出于无奈,还是出于真心就另当别论。
还有无数细节造型不必一一细说,比如电灯,蜡烛,比如门窗玻璃,比如室内兰花等等,每一个造型构图都有画外音。国内电影里除了《东邪西毒》外,我很少看过如此细致精致微妙的构图,能将画面的模糊与暧昧传达的如此充分。
不得不提醒一句的是,看这部电影时最好忘了84年费穆那一版,否则只能是对比时四不像的尴尬。
原文见博客:
http://yanhaibing.blogspot.com/2008/10/blog-post_29.html
2 ) 残垣断壁,春光微细
章志忱和戴礼言是同窗好友,玉纹和章志忱是从小在一起玩的邻居,戴礼言的妹妹戴秀,见到风度翩翩的章志忱更是心下欢畅。隔了几年的烽火烟云,人世扭结,各人已无从挣脱。玉纹16岁时,章志忱向她求婚,被玉纹家里拒绝。戴礼言和玉纹,应媒妁之约,成了夫妻。本不喜欢,结了婚,只有逼迫自己喜欢。种种不如意,令戴礼言脾气大变,身体也每况愈下,两人闹到分床而居,已是几年。膝下无儿女,床第无欢乐,都只在责任的范围里忍耐。
年华流转,玉纹也到底想着志忱,她拿自己精心培植的兰花,换西院书房里的霉味。她在戴秀16岁生日的晚上,穿上自己结婚时的衣服。她固执得可爱地要和志忱拼酒划拳,划的还是他们以前经常划过的拳。她像是几年没有进行光合作用的植物,终于遇见阳光,压抑而又迫不及待地重新生长。她还年轻,也还美貌。她心有不甘,他也只能望而却步。敏感的戴礼言,对妻子和好友的关系了然于心,他甚至想,如果玉纹嫁的是志忱,该有多好。他服下安眠药,以为以死能成全他们。但最后被志忱救过来,志忱离开小城,生活似乎又恢复原样。
《小城之春》最后,是四个隧道一样的出口,左边三个连在一起,都可看见出口之后的光明,右边一个又矮又小,像是死胡同。这部电影很安静也很干净,但是不闷,画面简单,但是有话。对话简短,但是话中有话。玉纹“我就来”,说了两遍,是拒绝之后的表态。“小妹妹,我告诉你,你今后没有16岁了!” 志忱对戴秀这么说,也一定说出了自己的隐痛。整部影片浅色着墨,内心戏却异常激烈。它把千秋家国和儿女情长放在一起,扼腕之余也心生悲凉。
不过电影的意义应该是积极的,《小城之春》的“春”,不是英文译名中简单的springtime,在中国的语境中,春极有象征意味,这种意味又相当统一为希望。大音稀声,大象稀形,这大概是导演田壮壮向导演费穆致敬的原因。
3 ) 如何讓戴禮言這個角色成為《小城之春》舊式家庭裏真正的主人翁 而不是被各種隱喻掏空的新皮囊
1948年費穆先生導演的《小城之春》日後評價甚高,地位尊崇,通常認為是有詩一般的意境,特別是跟整個紛擾的大環境相比,是一股清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跟張愛玲後來得到的公允評價是差不多的情況。2002年,田壯壯導演重拍《小城之春》,除了去掉女主旁白,增添改動一些場景與道具,特別是光影處理外,基本上就是照搬了費穆版的《小城之春》,上映後反響似乎不是太大,但還是跟當時整個紛擾的大環境,以及田導個人的境遇相比較,就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還是那個老問題,《小城之春》到底好在哪里?值得五十年後,用新的技術手段,與電影語言,依葫蘆畫瓢的再拍一遍?
在我個人看來,《小城之春》的好與特別,除了此類故事常見的含而不露的“隱喻”,與大環境的“逆行”,或者說是跟時代某種形式的“對抗”之外,更應該與之作比較的,還是曹禺和巴金那些創作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話劇與小說,講述大家庭的年輕一輩,面對整個時代巨變,因為排輩,地位與立場,還有性情的差異,所做出的不同反應……而這些故事因為不斷的以不同形式反復演繹,其中所包含的元素,也就更為讓人耳熟能詳,大抵也無非是反抗家長,出走私奔,忍氣吞聲,傳宗接代,投軍救國,家國春秋……
而《小城之春》自然是跟剛才那些故事不太一樣的,而且不僅僅是創作年份的差異,故事中的戴家也算是大家庭,房子不少,但因為戰火,已經被炸掉了許多,只剩下一些斷壁殘垣,門牆都有點形同虛設,從女主玉紋的旁白中可知,之前應該是有不少傭人的,眼下只剩下老黃一位,而家裏除了少爺戴禮言,少奶奶周玉紋,以及禮言的妹妹,也就是小姐戴秀之外,別無他人了。
這就形成了一個階層等級空白,逃難之後回到老家,家中可以說是沒了長輩的,戴禮言的父母去世了,而他因為體弱,夫妻分開住,也沒有一男半女,之前那種大家庭裏,必須被反抗的那種大家長,都不在了,而那種新生力量,更加新的一代,還沒被生出來,或者按這片中的人設與身體情況,是永遠也生不出來了……這也就大致相當於如果溥儀一家被趕出紫禁城後,沒有去天津和東北,而是到圓明園的舊址旁,用斷壁殘垣剩下來的石料與木材,蓋了間四合院,跟婉容與文秀住在裏面,沒有子嗣……
但這樣的隱居生活,顯然不可能平靜太久,很快就有一身西服的章志忱過來拜訪,他是禮言的老友,同時也跟玉紋青梅竹馬,只是多年不見,不知道這兩位竟然結了婚,而禮言也不知自己的太太與好友從小就認識。志忱的到來,吹皺了不只一池春水。這似乎又是再典型不過的民國三角戀故事,再加上戴秀和章志忱也很合得來,哥哥戴禮言還曾想撮合這門親事,這樣子感情的線頭就更多了。但問題還在於,跟之前那些沖出封建家庭,打破包辦婚姻不一樣的地方,是戴禮言雖然長兄如父,同時還是玉紋與志忱之間愛情的絆腳石,但他並不“反動”,更不專橫,他甚至還感歎自己體弱,對玉紋說如果她當初嫁的是志忱,那就好了,聽口氣和上下文,那似乎不是反話,也不是試探……
費穆版中是以周玉紋為旁白,貫穿全片,而田壯壯版中,雖然去掉了旁白,但感覺還是周玉紋和章志忱的戲份更有發揮,而扮演戴禮言的演員,一來有點少年扮老成,二來跟老片中那種特別的“口音”相比,新版演員的談吐,總還是有點古怪與出戲。但我覺得這不只是演員本身的問題,可能也不只是導演的,而更多是戴禮言這個角色本身的問題。首先,他太羸弱了,不但是身體,也是精神上,同時剛才也提到過,他這種角色在這種情境與關係下,一般都是反派,如《菊豆》裏的楊金山,由李緯扮演,也就是在費穆版《小城之春》裏演章志忱,又或者是《大紅燈籠高高掛》裏不顯山露水的老爺,也是同一類的,但戴禮言不一樣,他非但不做壞事,還反過來想“犧牲”自己,成就別人的好事。但這樣的角色,會引發觀眾的同情嗎?可能會有一點,但也不會太多,很多觀眾想來反倒會覺得他懦弱,在觀影口味上,很多人寧肯喜歡乾脆俐落的壞人,也不待見禮言這樣懦弱無能的好人!
但這也不是戴禮言這個角色最大的問題,因為在田壯壯的版本裏,章志忱看到梁上還掛著一副吊環,就回憶起當年戴禮言是全班第一個能做十字支撐的人,也就是說他當年體能很好。而另一方面,以家世,還有兩人當初的友誼來看,戴禮言就算是性情內向,但也不可能內向到哪去,也就是說,現在的故事,把這對曾經一樣意氣風發的朋友,日後不同的人生狀態,僅僅是描述成是醫生和病人的區別,有點潦草輕率,或者說有點太過隱晦……玉紋和志忱似乎是很痛苦,很有戲的角色,但實際上這三人之中,最有戲的應該還是戴禮言,但他身上這個病人的標籤,就把他死死困住了,而成了一個喻意的“空殼”,讓他自己,編導,以及觀眾都有點無所適從。
在比較兩版《小城之春》之餘,我還想起了格斯範桑特Gus Van Sant曾在1998年重拍過希區柯克1960年的驚悚代表作《驚魂記 Psycho》。和田壯壯處理費穆版本《小城之春》類似,格斯範桑特也幾乎照搬了希翁版本的情節與鏡頭,加以彩色化。本來除了這一點影壇軼事外,《小城之春》與《驚魂記》之間好象談不上有任何的聯繫與共通點,但不妨借用玉紋旁白仲介紹她老公禮言的出場時所言:我看他其實是神經病!
戴禮言與其說是身體的毛病,還不如說是精神上的,當然他沒有嚴重到人格分裂,變態殺人,但同時也不是說,他就不應該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與分析。中國傳統,甚至是當代對於人的關懷,大多還是表層,很少真正深入到內心。戴禮言可能很怕見光,總是檢查門有沒有鎖好,但實際上那門鎖不鎖早就沒什麼實際的意義,因為旁邊的牆都倒了。他可能有時會有幻聽,總聽到門外有鄰居家的孩子在吵鬧,叫老黃去趕走,但實際上鄰居家根本就沒有孩子,只是因為他內心其實非常想要孩子,但有心無力(影片中在對白中,也試圖給人一種戴家不是單獨住在這條巷子裏的感覺,但實際上全片沒有任何鄰居出現,如果在片尾告訴觀眾,戴家其實一家都是鬼,我想觀眾也不會感覺太意外)。
他沒准還有疑心病,總是懷疑玉紋會離開他,也懷疑老黃一直在偷他的錢,等偷得差不多了,就會逃走。但他內心還是善良的,也會體諒玉紋和老黃,因為換位思考的話,沒人願意守著他這個“活死人”的。而他的善良,有時候會過了頭,特別是章志忱來訪後,他先是怕章說起之前的往事,怕他,以及家人瞧不起現在的自己,然後又疑心他和玉紋舊情複燃,故而借酒裝瘋,極度真誠的要勸兩人在一起,畢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而他不想違背天意,成為絆腳石,叫老黃馬上拿文房四寶來,他立馬就要寫休書……
如果是這樣的話,戴禮言就不會只是形同一個封建沒落的象徵,而是在多種象徵意義的擠壓下,不得不變得扭曲,但始終希望找到出路的人物,而與他對比,玉紋和志忱就是再傳統與扁平不過的角色而已,他倆不再是小城春色的代言人,而得徹底讓位於複雜且多心,極端又立體的戴禮言。
從某種角度來說,田壯壯導演處理《小城之春》,還是太把這些演員,當成木偶,而且線頭還不在田導手裏,而是在當時已經逝去五十年的費穆導演的“遠程”操控下,同時也可能類似能劇的表演,一投手一舉足,著實也難為了這幫演員,雖然TA們大多所受的戲劇表演訓練,本身也是模式與拘束的,但現在畢竟談論的是電影。我個人覺得中國式表演或表達,還是像很多東西一樣,處在兩個極端之間,既不能像日本那樣完全程式化,以及良性的繼承傳統,又無法像歐美那樣銳意進取,打破框架,就總是在兩難之間,如果處理不好的話,那就是兩邊不靠,四不像,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這種微妙的“尷尬”,其實也就如同《小城之春》中的戴禮言這個角色,倘若盡情渲染與放大這份“尷尬”,那“尷尬”就不再是尷尬,而是斷壁殘垣也遮不住的,真正的小城之春。
4 ) 浅评《小城之春》新旧版
田壮壮翻拍的《小城之春》2002年版怎么看都比1948年的老版要强要好,田导更擅于用镜头语言讲故事且知道如何讲好故事。
第一,2002年版的摄影、用光讲究、漂亮多了,白天是青灰、灰绿的冷色调,夜晚均是大面积的黑色,仅用桔色的光打亮、凸显人物。1948年老版太太窝在小破房子的一角刺绣,2002年版改至倚窗剌绣,有时侧光有时背光,那种秀美的孤寂,拍得如画儿一般;
第二,场景布置、选择更为恰当。2002年版镜头下可见高大斑驳的院墙、可见天井梅枝、古亭甬道、回廊翘檐、中式家具、古董瓷器……在昏暗、陈腐、颓败的气息中仍可瞥见昔日深宅大院、书礼之家曾经的阔大与考究,可1948老版只看到残垣废墟,逼仄小屋,并无丝毫往昔书香大户之气,所以,其电影镜头语言与主人公的旁白是不符的;
第三,出镜演员造型更到位,如新版礼言改蓄了小胡须,更像旧式破落大户人家的少爷:其太太玉纹1948年版里脸大身粗,粗糙土气,缺乏女人之阴柔,2002年版里则绢秀静雅,举手投足间方有了曾经好人家的少妇韵味,尤其那几袭不一样的旗袍,更增添了玉纹的窈窕妩媚,这也是老版无以比拟的:小妹戴秀也是,1948年版的演员傻乎乎胖嘟嘟的,瞅着何止16岁呀,扮相老气,2002年版才真正与故事相符,是个淘气可爱单纯的女学生!
第四,废除了1948年原版那别扭的旁白,原版安排女主玉纹旁白,来叙述故事、心情,真挺怪异的,2002年新版则全改为镜头语言了。
第五,2002年翻拍版在故事的总体架构上是忠实原版的,但在剧中人物的一些语言、动作、布景、情节等小细节上则进行了调整、完善,使之更合情理更符合故事的推展,而不是像原版那样唐突、生硬;
第六,2002年版的配乐棒多了,更好地烘托渲染了气氛和情绪。
总之,我毫不犹豫地给予田壮壮2002年《小城之春》版4星,原版摄于1948年,在那个年代应该算是相当不错的作品了,但今日观看起来,不免觉得稚嫩青涩,我无意于贬低老版《小城》,但对不少蜂拥而至鼓掌高评原版而低估针砭2002年翻拍版的,讲真的,我不敢苟同也不大能够理解。
5 ) 婉约佳作
记得当时看完《小城之春》,我在豆瓣上写下的感受是:“好像要发生点什么东西,又什么都没有发生。”事实上,影片委婉细腻,意在言外的氛围确实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挺喜欢这部电影,只是很烦男主人公的妹妹。演小妹妹的演员专业一定学得很好,声音洪亮吐字清晰,可惜她爽朗的声音总是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她的表演跟影片内敛含蓄的氛围极不相符。至于演玉纹的那个女子,我倒是认为她拿捏得恰到好处。她略嫌生硬青涩的举止常常能让人感受到冷若冰霜的脸下暗藏的热情跟欲望。至于两个男的就不多说了,对比鲜明,形象立体,均与影片氛围配合得天衣无缝。
豆瓣上关于影片故事的简介写得极有水平:“小城黯哑的城墙垛子,卧在乍暖还寒的季节。一夫,一妻,一妹,一客,再加上个老仆和几只待客的鸡,五个人一个大院,几天的时间.……在这样一个时间、空间凝固的处境里,一个旧人突然出现。他是夫的好友,是妻曾经的情人,是妹心中的爱人。他们眼神的闪烁,心头的颤动,一波波细腻的情感波澜堆积成了那一年的‘小城之春’。”
写得比我好多了,寥寥数语就把故事极其氛围交待得清清楚楚。影片最成功之处在于它没有陷入叙事的俗套,而是通过不易为人察觉的细节来表现这个故事。比如志忱刚刚到来时与玉纹的相遇,他们嘴巴上说着非常“礼貌、客套”的话语,而眼角眉梢却时时流露出或疑惑或失望或兴奋或缠绵的复杂内容来。这让比电影里常用的“桌底调情式”高明许多,少了桌子的掩护,当着丈夫的面不动声色地与情人交流无疑需要更高的技巧。他们做到了,至少我一眼就能看出玉纹跟志忱的关系决不简单。
等你沿着导演为你铺垫的情调往前走的时候还能在电影里发现很多处表面上风平浪静,内地里却波涛汹涌的场面。所以,玉纹绝不像他的丈夫礼言描述的那样“冷”,在爱情面前她也炙热得像团熊熊燃烧的火焰。
最终,在一场生日宴会上,玉纹跟志忱的婚外恋已经发展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仿佛只要一个轻微的暗示他们就能突破重重枷锁投入彼此的怀抱。然而他们还是忍住了,茫茫长夜,几人轮番上场,都为自己的辗转反侧向礼言讨要安眠良药。这时,礼言也察觉到了妻子与志忱的微妙关系。故事发展到这里时,老屋虽然依旧沉默,可是屋内的气氛却剑拔弩张,紧张到了极点。可是,影片却迅速把我们引向了另外一个方向:为了成全自己的妻子跟好友,礼言居然服药自杀。
志忱跟玉纹要是强硬一点狠一点,他们的爱情也就到手了。在关键时刻,他们还是流露出老百姓常有的软弱跟善良。出于良知跟道义,身为医生的志忱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救回了礼言。这样一来,玉纹与志忱的这段爱情插曲也只能悻悻然无疾而终。所以我才说:这部影片是“仿佛要发生点什么,终于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电影的小题材小场景限制了它的格调,也许它的小打小闹会让人觉得影片繁复啰嗦,不大气。但摒除门派之争,在婉约派的艺术领域里,它绝对是部经典之作。
6 ) 新旧两版《小城之春》对比
一、新版取消了女声旁白。个人以为,原版的旁白在点明人物心境和每个人的性格上作用很直接,而且不冗余。
二、城头的作用明显削弱了。开头时,玉纹象征性地在城头上出现了一下,而旧版则花了几分钟,而且配上独白,说明她的苦闷。结尾时,新版以玉纹在窗下刺绣而结束,而旧版又回到了城头。小城之春,这春色在新版里是院子里的红花,而在旧版里多半是通过城头。城头的作用既弱了,那么郊游、私话都选在城头,就没什么意义了。
三、三人的出场,在旧版里,一一花个几分钟,但是新版里通过一系列剪接,变成一个横向的进行。尤其是志忱的出场,少了老仆人往街里洒药的情景是一个遗憾,而且通过老仆人与他的惊喜相见,其实更能衬托出志忱从前与李家的密切来往,而新版里用直写李与章的叙旧,未免不够含蓄。
四、玉纹与志忱的见面。旧版中,玉纹在见面前已经得知是旧情人,心情之纷乱是精彩之笔。新版中完全不知情,而见面后也表现平淡,又没有旁白,后面的旧情难忘很是突兀。
五、玉纹的梳妆。新版中,玉纹时常对镜梳妆,仿佛只是一个爱美的女人。但是,旧版中玉纹的梳妆都是在与志忱相见之前的,足见她的用心。
六、新版增添了志忱去小妹学校跳舞的情节,为的是表现志忱的个人魅力。旧版不刻意说志忱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
七、仆人老黄,在新版中话多了很多,而且是江浙口音,似是暗示一个南方小城。
新版虽然在人物造型上努力靠近旧版,甚至连讲话都有意放慢语速,但是形似而神不似,相去甚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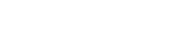




















相比较于老版,江南意象更浓,演员表演更细腻。
昨儿在资料馆2号厅重温1948年版时,冒出了观看2002年翻拍版的念头:开场的几个镜头让我误以为本片要将《小城之春》的故事拍得更加写实生活化,结果,大量的缓慢推移长镜头+演员们偏话剧形式的表演,使得整部看起来更像是舞台剧化,至于在原版的基础上修改的部分情节也是喜嫌参半……累,一度看睡过去。
阿城將玉紋旁白拿掉,田壯壯又要李屏賓把鏡頭拉遠,使故事由第一人稱轉為第三人稱;雖然在禮言和志忱的背景上多描幾筆,演員們重新詮釋的對白卻不再寫實而彷彿邵氏電影的配音……全文:http://hou26.org/zeta/golden2004d.htm
几乎复制,但隐去了女主独白,替玉纹包扎伤口的由章志忱变成了丈夫戴礼言。李屏宾的推轨摄影,静谧悠远。
各种大咖,看时还奇怪哪个摄影师运镜这样好,竟是李屛宾,美术也很扎实,置景服装道具都棒,叶锦添真是百搭。片中摄影和美术营造出凄清的东方意境,与一场一镜的调度配合的恰到好处。划拳一场戏调度超凡,人物走位与焦点来回变换,难度极高。气氛营造成功,基本上可以说是最好的翻拍片,离五星只差一点
☆:4- ♡相较于原作输在“聒噪”,台词、运镜、剪辑各个方面,像涂太满而不留空的画,尽管确实丰满了空间并填充了心理背景;演员的表演也稍嫌过火;一切都太实了,也没有积累起来的情绪。一种对立感更加被强调,一中一洋,被置换的歌曲,由此引出的摇摆立场与选择,未曾真正现身的上海/一种吸引力,不知道是不是基于对原作的解读或研究之上。但是仍然,两千年过了,感谢还有导演愿意翻拍小城之春,以一种真诚的态度。
毕竟是致敬之作,田壮壮并没有对费穆原作做太大改动,除了画面变成彩色、隐去女主角的内心独白、主角里少了几只鸡之外,其余基本照搬过来
果然是一次像前辈的致敬,在他的年代,用他的方式,有他的理解和探索,也有向费穆导演的学习和传承,很好的驾驭了李屏宾的摄影风格,也拿来了李屏宾式的东方神韵。
电影中四个人之间包括爱情、亲情、友情在内的情感纠葛,却经常以三角的动荡关系来叙述,这使得极简的场景蕴含着巨大的并不喷发的内在矛盾。近乎程式化的表演看起来青涩而有些虚假,但是同时,配合着简单的镜头仿佛作出了内涵大于形式的象征,这应该算是一部能给人充足回味的电影。
拍法上基本就是固定机位+摇摄,基本上就是各种摇摄,造就了一整篇的移动。后景无疑是在变化的,人物也是在运动的,都是在强调运动性,这是在和费穆做区别和旧电影的形态做区别。回看故事,细节上改得挺多的,悄然地置换成了现代语境,你会发现人物的反应就是这个变化后情景下的产物。但所有的一切却都没有落在针尖上,演员的表演和旧作比较,效果居然是相反的,表演之下是不自然的状态,人物失了魂。人物之间的对白,剧情的改动都让很多情感的表达不见了,其容量不够你感受。2022-05-23重看。大部分表演都是当代感受的激发。小妹生日众人围桌喝酒那场戏调度有意思,丛一开始礼言背对观众到自主做到中央面对观众,再到被众人挤出画外。实在是可怜。剧本改编是阿城,摄影是李屏宾。看了花絮,理解了一些拍摄理由。
以前的电影,真含蓄,那些小情绪也真够美的。听说这是田壮壮的翻拍,不知道老电影还找不找得到。我喜欢老黄那口不标准的普通话,听着很贴近。
「小城之春」好便好在情绪的一种持续的流淌,隐忍压抑而不外放。情绪的体现靠行为。这里,情绪多次被打断,多了情绪直接表现,哭泣喜悦一览无余,也便少了逐步积淀之后的集中呈现的张力。少了内心独白,便少了一层表现的空间。女主行为的略微差异却改变了故事内核。原版结尾多好。
3.5 与老板无奈、落寂和破败的基调相比,新版从画面取舍和环境的刻画上更多的是一种压抑和阴郁的感觉。新版更加注重画面的流动性,多使用长镜头的移动,有一种欧洲式的凝练,但因此在人物的关系和活动的细节上则远无老版刻画得细致。表演和人物外形有点感觉不适,结局没有老板的希望,但表现得也挺好。
江南女子软软细细的声尾,有一点慵懒和倦怠。她在春日孱弱的光线里绣花,是百般的心无所踪。破败的旧院,久病不愈的丈夫,开始有萌芽意识的小妹,对她而言,都是外物,可有可无。甚而连带她自身,她也怕是要完全摒弃和忘记。唯一坚持的是与丈夫之间的距离。那里面有一道墙,在这段婚姻开始以前就构筑。
一直说随便,却不曾随便地私奔;一直说无碍,却不敢无碍地偷情。你就像春风一过,荡舟的歌,划拳的酒,枝杈上的手绢,残垣边的夕阳都春意盎然。我把房间的灯都拉开,反正生活总会将它们熄灭。其实,没有恨也会有战火,没有爱也能有婚姻,没有心跳也能叫活着,没有花开也可以叫春天。反正,也都没有你。
8分。2023.3二刷,这是中国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讲述民国年间的人们是如何搞暧昧的。同时也有象征意义,一个病恹恹的老长衫与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思想。另外,女主胡靖钒真的是一个眼睛会说话的演员。
更大更绿的小城,平面外化的改编,志忱和玉纹的屋内对话,声音好像不在同一空间,还记得原版玉纹扑哧一笑后直接趴着哭,多次走路节奏的差异,原来的雕琢没了...《花样年华》才是有所继承有所开拓的改编吧
虽然开场就摆明了上限,但还是渐入佳境。表演的相对生活化消解了原版的非自觉间离性(所谓话剧感),大量无意义的镜头运动却又平添了廉价的电视剧感,中间教跳舞的戏把封闭感破坏得莫名其妙,城墙边的几场戏是创新意识最集中的部分。但无论如何,在色彩和声音上做文章是最理所应当的,所以只开发到这个程度(包括去独白)很难不让人质疑翻拍的野心和诚意。结尾那一收,是全片唯一不一言难尽、有功无过的改动了:同样“止乎礼”,却不再有相依城墙的一幕,一怔一叹一个空镜让人物状态从主动落回了更缥缈也更可信的被动,意蕴和多元的指向都有了。但依旧是局限于文本而非视听的破立。后知后觉,论气韵的继承和重构,《花样年华》是真正的当代《小城之春》。
在死水里扔一块石头
不觉得田壮壮比费穆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