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扎马,一个出生于南美的西班牙军官,等待一封国王授予他更好的位置的调令。他的处境很微妙。为此,他被迫顺从地接受每项任务。当然,国王的命令从未到来。当发现等待是徒劳的时候,他决定参加一个危险的任务,以期让国王听到他的事。然而,当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他发现他唯一的愿望是活着。陌陌影视陌陌影视樱花影院6080影院夺命回声寓言赤焰战场(国语版)佐罗的印记1920柠檬糖的魔力喇家史前文明消逝之谜遥远的召唤公主与青蛙(粤语版)让爱做主王志文版李茶的姑妈侠女闯天关执迷大兵小将走进四九城乱反射玩转澳门加倍Fun火海凌云(原声版)伏妖白鱼镇2小猪班纳第二季胶囊计划电影人寡居的一年为人父母第五季铁甲钢拳仓储挖宝王第1-5季黄金路
长篇影评
1 ) 《扎马》的感官体验、多孔性与救赎——对卢奎西亚·马特尔的本雅明式解读
作者 / 吉列尔莫·塞维利切(Guillermo Severiche)
翻译 / tunmii
首发于《拉美电影迷宫》公众号://mp.weixin.qq.com/s/vfVwDCk1TShnTqAdtAZZJw

“卢奎西亚·马特尔穿着轻便的衣服……她看起来就像一个十九世纪的探险家,又像是一只21世纪的珍稀鸟类”。
——《漩涡中的猴子》,塞尔瓦·阿尔马达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格尔德·盖蒙登(Gerd Gemünden)强调了卢奎西亚·马特尔的电影通过声音和触觉语言来吸引观众的能力。更特别的是,盖蒙登认为,马特尔的电影坚持人类经验中的短暂性、偶然性和碎片化质量。他补充说:"感觉、触摸和嗅觉不仅仅是使人类脱颖而出的行动要素,也是诱导观众感官知觉的形式" (Gemünden: 2019, 7)。就《扎马》(2017)而言,盖蒙登的前提允许我们去探索两种不同的观赏模式,而感官层面于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一方面指向了一种以便于读取十八世纪历史实际的声音和触觉资源的方式;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到它与观众的关系,通过感官来再现历史有什么政治含义?本文借由可能的分析方式,对《扎马》的感官维度、与观众的主体间联系以及殖民地历史进行重新解读,探讨被官方历史话语所统治的政治。
为此,我从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的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关键概念。其一为《论历史的概念》,于1947年追授出版;其二是《那不勒斯》一文,最早出版于1925年。虽然这样的关联似乎是随机的,但或许可以在本雅明的文本和马特尔的电影之间建立一种对话,以证明电影对历史——一种合理化胜利者的统治以及被征服者的流离失所的政治、文化话语——的质疑。从本雅明的这些文本中,我一方面采取了历史目的论的概念,重新定位观众的角色从而制定历史,以达到反对官方话语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空间组织者的多孔性概念重新制定了叙事空间中的社会限制。不论是哪一种读法,感官平面都起着决定性作用。首先,《扎马》的感官维度邀请观众将自己置于殖民者身体的破碎体验中,《扎马》的感官维度邀请观众将自己置于殖民者身体的破碎体验中,感知到了奴隶、黑白混血儿和土著人的存在是对欧洲人或克里奥尔人的脆弱性主导力量;其次,影片通过展示不同的僭越与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跨阶层性行为,以呈现出不同社会等级之间的模糊界限。
卢奎西亚·马特尔电影中的感官平面
《扎马》是由安东尼奥·迪·贝内代托(Antonio di Benedetto)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该小说出版于1956年。马特尔保留了原文中最重要的叙事元素。迭戈·德·扎马是西班牙王室的一名官员,他等待着国王的调任公函,以使其前往他的妻子和孩子居住的城市莱尔马。他在(现今)巴拉圭的领土上待了许多年,这个地方与河流、丛林和原住民社区接壤,并在努力保持着当局的青睐。东方人的拜访——一个有着经济关系的朋友——使他与卢奇亚娜有了往来,她是一个在社会上声名显赫的西班牙女人,以独立而闻名。他寻求与她交欢,却没有成功。几年过去了,尽管他凭借努力和辛劳忍受着总督们的戏谑,但国王的信函从未到达。在绝望中,扎马决定加入一群勇士,进入丛林寻找危险的恶棍皮库尼亚。然而,这次冒险使他陷入了更大的困境,因为他被不断的威胁所包围,最终致使他双手被截断,生命垂危。
《扎马》标志着马特尔的电影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与她之前的故事片(《沼泽》、《圣女》和《无头的女人》)不同,《扎马》没有发生在她的家乡萨尔塔,没有女性作为主角、没有游泳池,也没有质疑当代阿根廷富裕中产阶级的特权和颓废。然而,影片保留了区别于马特尔风格的电影配置:例如,对声音的特别关注和对场外之物的暗示。这些资源构建了一个感官维度——在这个维度之中,人物的身体体验被前置,并呼吁与观众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在另一篇作者研究中,黛博拉·马丁(Deborah Martin)认为,马特尔的电影构成了当代致力于电影感官美学趋向的一部分,即将触觉和感觉置于视觉之上(Martin:2016,7)。此外,根据马丁的说法,马特尔的电影进行了一个 "实验",由 "感知的危机"首当其冲(马丁:2016,13)。许多在泳池或床上的场景旨在发展一种边界状态,一种物理层面的不确定性,其中,影片中的人物和观众都会质疑现实是否是它看起来的样子(马丁:2016,13)。马丁强调,其坚持通过声音效果或对影响感知的视觉图像的处理(如人物的失焦)来展示梦幻、迷惑感或溺水状态。

除了盖蒙登和马丁的研究之外,其它文本也涉及到了马特尔的电影与观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感官层面的研究。二十一世纪初,人们开始了所谓的 "情感转向",不同的作者批判性地关注情绪和情感,将其作为理解经验的背景和场所的输入(Caña Jiménez and Venkatesh: 2016, 176)。特别是在电影研究中,吉尔斯·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最初假设与劳拉·马克斯(Laura Marks)和维维安·索布查克(Vivian Sobchack)的研究一样产生了主要的影响。在拉丁美洲层面的理论框架内,伊内拉·塞里莫维奇(Inela Selimovic)将马特尔与其他当代阿根廷女导演(如阿尔贝蒂娜·卡里和露西亚·普恩佐)进行了比较。她使用 "momentos afectivos"(情感时刻)一词来强调她的电影与观众之间所建立的人际交往,从而带来与记忆、暴力或欲望有关的社会政治潜台词(Selimovic, 2018: 11)。米茜-莫罗伊(Missy Molloy)则解释说,马特尔和卡里的电影不是通过可识别的叙事情境来鼓励与观众进行联系,而是通过人物的身体体验(Molloy: 2017, 96)。
这些研究马特尔电影的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主体间性的概念作为研究电影和观众关系的主要语义平台。值得一提的是塔利亚·莱因(Tarja Laine)的研究,她于其中对主体间性的定义如下:“主体间性关注的是自我的那个维度,它将主体与人际关系性的世界直接联系起来;在那里,集体经验的‘外部'成为主体心理生活的‘内部'” (Laine, 2007: 10)。她解释说,为了理解主体性,必须考虑主体与他者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可以反映在观看电影的经验中,因为观众可以发挥自身身体的整个情绪和感觉系统(Laine, 2007: 10)。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强调了《扎马》的这种主体间维度。其中,电影可以吸引观众的身体体验。但正如塞利莫维奇所指出的,这种感觉平面包含了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兴趣,超越了叙述论点本身。
对历史话语的干预:马特尔和本雅明
现在,对于《扎马》,这些社会、政治问题是什么?尽管许多关注点都于此出现(种族主义、社会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妇女性行为),但值得关注的是这部电影中的新内容——对殖民历史话语的反思。在各种采访中,马特尔解释了她在执导《扎马》时对历史和历史电影的态度。据马特尔所说,这部电影由“纯粹的发明”构成(Martel, 2018a: 37)。此外,马特尔的面向的不是历史,而是现在:“我所做的是发明一个过去,就像发明科幻小说一样[……]这部电影是以同样的方式制作的,借助于某些元素,把现在向过去投射,使我们能够将这种话语置于历史"(Martel, 2018b: 45)。
马特尔在她之前的电影中探讨最多的主题之一便是她的家乡萨尔塔的明显的社会阶级差异,其中白人中产阶级对臭名昭著的土著贫困阶级实行统治,亦或享有优越的社会等级地位。马特尔的这一声明,明确了她将观察过去作为一种兴趣,以此扩大对社会阶级、种族和统治的批评目光。换句话说,马特尔的电影通常将这些权力动态视为殖民历史的遗留,这些遗留在今天的萨尔塔仍然存在。因此,《扎马》可以作为不平等社群的一个历史例证。然而,马特尔不仅展示了这一现实,还创造了其他的动态。其中,被征服者则有了一个更密切相关的机构。

这种指向当下的对过去的虚构,颠覆了殖民史电影的陈规和概念。在我看来,这就是卢奎西亚·马特尔最富新意的批评。正如瑞恩·吉尔贝(Ryan Gilbey)所写的,“由于其薄弱的恐慌、偏执气氛,以及《扎马》中奴隶所经受的苦难远未逾越现实中的苦难,这部电影永远不会成为殖民主义的代言人”(Gilbey, 2018: 53)。此外,这种对殖民主义的反驳也可以从对天主教会的绝对消除中看出来。马特尔解释说:“我想创造一个没有天主教的世界,即使从历史来看这是不正确的。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教会的力量并不那么单一,世界是更加多样化的——因为权力无所不及”(Martel, 2018a: 37)。
为了更好地确定马特尔放置于《扎马》之中的对于历史世界的哲学立场,并分析电影于知觉层面的作用,我认为必须提出瓦尔特·本雅明对于历史的主要假设。我认为,这些本雅明式的概念在定义马特尔的观点及其对电影的影响方面,起到了实际的批评作用。在《论历史的概念》一文中,本雅明严厉批评了在他那个时代享有霸权地位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或历史主义解释——在其中,历史被认为是进步的,是一连串的事件,它毫无辩驳地指向了对未来的救赎。因此,“进步”仿佛成为一个准宗教般的实体,一场对弥赛亚的顾盼。置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主义的恐怖中,本雅明失望地观察到这种历史主义话语的欺诈,提出要与这种理解历史的方式决裂,并关注构成历史主义话语的基础——历史时间。其中,历史时间成为 “一个同质的、空洞的领域,事件在其中‘发生'”(Echeverría, 2010: 31)。与此相反,本雅明在论文XIV中提出:
历史是一种建构的对象,其位置不是同质和空洞的时间,而是充满了‘现在的时间'(Jetztzeit)”(Benjamin)。这就是说,历史时间包含了一种断裂的潜力,允许从未来的角度对过去和现在投以新的视角。这种“现在时间”是革命性的,从历史的连续性中出现,尽管其因需要艺术家或革命家的干预从而不是自然而然的。这个“现在时间”打破了唯胜利者所书写的固有历史构造。

根据甘德乐的说法,本雅明从神学中获得了中断“时空连续体”的想法,并将这种断裂定位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时间’不是最后的审判,人们不必通由等待自身的死亡以接近这个全新的时间概念"(Gandler, 2010: 52)。本雅明以一种跨越性的方式构思了历史时间,从一个裂缝中逃脱了历史主义的进步概念,即胜利者的话语。过去以物质的形式存留在我们的现在,在这种存留中,有“现在时间”的存在特征。它自身位列于文化物品中。本雅明认为,虽然每一个文化物品都是胜利者的标志,但它是对被征服者的野蛮行为的描述。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保持远距离的观看,从历史时间的断裂处观察,挽回被征服者被遗忘的存在。这就是本雅明在论文VI中所提出的 "微弱的救世主力量":
历史地阐述过去并不意味着 “按照真实的情况”去认识它。它意味着要在某个危险的时刻抓住记忆的闪光点。……在过去,点燃希望的火花是一种天赋,这种天赋只能在意识到这一点的历史学家身上找到:如果敌人获胜,即使是死去的人也无法安置其身。而这个敌人将会一直取得胜利。
正如迈克尔·罗维(Michael Löwy)所补充的,“‘美德’对历史学家来说正在于反对现实的暴政,在于‘逆着历史的波浪游泳'”(Löwy, 2010: 36)。这便是在试图救赎堕落的人和被征服者时仍然存在的希望,是一种对过去的审视。“希望并不是来自未来,而是来自于那个抵制敌人统治的、被打败的胜利者的过去。(Beiner, 1984: 426)。然而,这个“危险时刻”也包含了从“今天”开始面对“过去”。“过去”不再是可辨识的、可被超越的物质,而是一个经转化的实体,作为当代的支柱而存活。正如甘德勒所解释的,当我们反思过去的记忆,并对我们的现在有了新的认识时,过去的记忆图像就会变成现在的,成为此时此刻的一部分(甘德勒,2010: 63)。这些图像已经存在于我们之中,只是我们需要放下从主导的历史主义话语中所继承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对它们进行去粗取精和活化。正如娜塔莉亚·塔凯塔(Natalia Taccetta)所扩展的,艺术作品的一个优点正是对某些对象的历史位置提问,并在新的感知中对其形象进行重新定位,不以服从时间顺序来破坏对现在的感知(Taccetta, 2017: 16)。
扎马的感觉平面、历史时间和孔隙度
可以说,马特尔的作品并不是唯一一个为拉美殖民历史中被征服者的地位进行平反或救赎的作品,因此,它被刻在本雅明在其文本中发出的呼吁之中。有经典的电影,如《最后的晚餐》(托马斯·古铁雷兹·阿莱,古巴,1976)或更现代的电影,如《瓦赞蒂》(丹妮拉·托马斯,巴西,2017),电影中的主角为奴隶、黑白混血儿和其他被欧洲殖民力量所征服的人发声。然而,《扎马》从马特尔的电影作品中脱颖而出,同时保留了导演的风格线索,这值得进一步的分析。电影的感官和声音平面与观众建立了主体间的关系,因此,救赎行为也是一种身体行为。声音的使用和对身体感官的诉求使我们考虑到两点:(1)殖民者身体的弱点和脆弱性以及 2)一个与欧洲人、克里奥尔人明显并存的他者社群的威胁和实际力量在不断增长
迭戈·德·扎马的身体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到达殖民地领土后忍受着艰辛与疾病的身体。例如,疾病与身体的逐渐腐烂在某些人物身上得到了体现。在影片开始时,他的东方朋友告知扎马他的身体很虚弱,这一情况在接下来的场景中更为恶化。在卢西亚娜的家中他喝了一些酒,离开时,其胃部的疼痛和痉挛声清晰可闻。扎马试图为他的朋友寻找医生或治疗师,但陪伴他的男孩也最终死去。尸体被安置在教堂里,用石灰覆盖以防止其严重腐烂。

在被逐出家门并被剥夺物质财富后,扎马也得了重病。镜头详细显示了他被汗水浸湿的皮肤、他的颤抖和因发烧而逐渐瘦弱的身体。后来,在战场上与战士们一起的另一个人物——即队长——向扎马和其他人展示了他那只肿胀腐烂的手。他说,在他睡觉的时候,一种刺痛把他弄醒了,显然这来自蜘蛛或黄蜂。在接下来的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手和胳膊逐渐腐烂的过程。最后,当皮库尼亚·波尔图(Vicuña Porto)截断扎马的双手时,发生了痛感层面中最强烈的物理时刻。


除了视觉层面的感官体验,影片强调了声音的效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特尔首次使用的谢帕德音(Shepard)。这些功能显示了对稳定情绪的深刻影响,其中不一定有任何视觉上的指示。谢帕德音是一种声音效果,在其声音序列中创造了上升或下降的错觉,而没有一个明确到达的终点。因此,它产生了永无止境的紧张、运动或下坠效果。根据埃利奥诺拉·拉潘(Eleonora Rapan)的说法,在《扎马》中使用谢帕德音调,首先应该被解释为对坠落的象征性表述(Rapan, 2018: 138)。
在这种效果出现的前三个场景中,扎马都处于一种遐想或强烈不悦的状态。第一个场景是当东方人和他的儿子来到殖民地时。这是一个被悬挂在奴隶背椅上的孩子。孩子喃喃地介绍了扎马是谁,他的过去和他的社会地位。然而,当孩子沉默无言的时候,声音却仍在继续——这个场景可能仅仅是一个幻觉,尽管这一点并不明确。第二,就是在卢奇亚娜招待他和东方人敲打一些杯子时。在这里,玻璃的声音开启了谢帕德音的使用;扎马进入了一种疏远、混乱的状态。第三次是在与州长的会面中,扎马得知他的秘书文图拉·普里托将被驱逐并转移到勒马,也就是他自己想去的地方。在这些场景中,谢泼德的音调是下降的,这让我们可以推断出,声音是用来强调角色正在经历的、未被彰显的情绪紧张程度。
拉潘注意到了第四个场景,在这个场景中,谢泼德的音调是上升的,并唤起了另一种与扎马的情感和身体有关的层面。在他被赶出房间后,扎马在郊区一个破旧的寄宿房里寻求庇护。在那里,他病倒了,被高烧折磨。这里出现了影片中最后一次谢泼德音调。拉潘解释说:"这也许与扎马的高烧有关,谢泼德音现在似乎更多地与他的的身体状态有关,而不是明确地与他对调任的无望感有关。"(Rapan, 2018: 140)。那么,这种音效不仅进入于人物精神状态突然迷失的时刻(Rapan, 2018: 140),还强调了他愈发虚弱的身体状态,在整个影片中指向了一种无休止的螺旋式下降。乔瓦尼·马尔奇尼·卡米亚(Giovanni Marchini Camia)明确指出:"这种诱发焦虑的声音效果给人一种无限下降的错觉,而实际上人们陷入了一个不断重复的循环"(Marchini Camia, 2018: 54)。就像马特尔之前的作品一样,她的人物总是沉沦于一个逐渐腐烂的过程之中。
这种多样的视觉和声音工具使影片具备了主体间一种交互的感官质量,人们能够更多地进入片中人物的身体和情感、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与依靠光学使得观众与银幕保持距离的电影不同的是,感官上的吸引力引起了对人物更全面的、整体的身体认同。
这些手法首先使得我们对欧洲人和克里奥尔人脆弱的、被削弱的生存情况进行描述。这一特点与《扎马》之前的三部曲中萨尔塔的上层中产阶级的表现方式相吻合。然而,感官层面也与其他观察被官方历史所取代的人类群体的救赎意图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最开始的一个场景中,扎马不得不带头审问一个戴着手铐的印度人,他正在痛苦地呼吸。当他被释放时,他跑到墙边伤害自己,倒在了地上。他在那里喃喃自语,讲述了一个一条无法离开溪流的鱼的故事,这将是对扎马一系列冲突的预言。虽然这个印度人看起来被俘,但他似乎完全没有被支配。这种表述——将被殖民的主体作为自己行动的代表,或自身命运的掌控者——在整个影片中反复出现。这种想法随着恐吓扎马的幽灵儿童的出现而再次出现,土著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们鄙视他;丛林中强大的嗜血土著抓走了他、剥夺他的财产。非洲奴隶和黑白混血妇女也有他们的自主权:他们是进出自允的信使,他们有自己不服从于殖民者的信仰;他们蔑视扎马,自身便成为了幽灵或死亡的化身,在生病时对他进行恐吓。

在这些人物中,卢奇亚娜的奴隶马兰巴地位非常突出。马兰巴因逃离前主人而受到惩罚,她的脚底因此致残,并感染了一种有毒的植物。马伦巴侍奉卢奇亚娜时的一瘸一拐正是前后事件的连续体现。她的失语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抗议行为,因为她“有自己的舌头”——如卢奇亚娜所说。除了由殖民者所造成的痛苦,她表现出的总是独立和坚强。在影片开始时,马兰巴注意到扎马在看她和其他裸体女人洗泥浆浴;扎马逃走了,但马伦巴追赶他。根据盖蒙登的说法,“马兰巴对扎马行为的反应是勇气和族群意志的标志” (Gemünden, 2019: 111)。
虽然这些人类群体作为一个强大的他者出现,但影片的感官层面主要定位于主人公扎马的身体体验中。因此,奴隶和原住民构成了扎马无法理解的两极的另一面,它恐吓、威胁着他。恐怖类型的电影帮助马特尔去强调这一点。扎马生病期间与黑白混血的鬼魂在一起,一系列的恐怖场面、内院奇怪的仪式、夜间在丛林间行走的盲人土著族长的到来,以及土著战士对白人克里奥尔人的抓捕和折磨等就是一些例子。电影的感官层面也由此构建了扎马这一被削弱的肉体——马特尔似乎同情地看待他——他常常感到不适或恐惧:那些更强大、更独立的他者群体都在鄙视他。


这种对殖民地历史的处理,使我们可以把影片中本雅明式的历史救赎视作一种行为,它也对应着声音和对身体感觉的诉求。然而,我想提出本雅明的另一个概念——多孔性,以便考虑电影制作和哲学分析之间的另一个优势。相对于上述内容而言,“感官”再次作为分析的要点出现,但不再是从疾病或痛苦的角度,而是从性欲的角度。
本雅明与阿斯哈·拉基斯(Asja Lacis)一起在1925年发表了他的文章《那不勒斯》(Nápoles),其中他从感官角度对城市的结构的进行了评论。他从一个沉浸在这个地方的主体视角来描述这个空间,以便感知构成城市的不同社会、经济、文化和时间层次和边界。本雅明用“多孔性”一词来确定并说明构成那不勒斯的所有社会层面之间的渗透性和相互渗透性。他提到了城市的建筑(Benjamin, 1979: 169)、文化生活(Benjamin, 1979: 171)、私人和公共空间(Benjamin, 1979: 174)。根据艾因·欧海利(Áine O'Healy)的说法,本雅明的“多孔性”成为了获取知识的一种模式,因为它指明了事物表面的断裂,并给予了去发现那些隐藏于日常的事物的可能性(O'Healy,1999:241)。正如本雅明所解释的,文本中描述的节奏那不勒斯在通过一系列生动的空间时,揭示了一种运动,逐渐模糊了一个空间和另一个之间的界限(Benjamin,2005:37)。公共的和私人的,古代的和现代的,本地的和外国的;它们相互重叠,模糊了彼此之间的界限,重合在一起。“多孔性”的概念不仅是一种观察和登记空间的方法,也是一种作为概念而构成的认识论,其允许我们将社会文化单位视为没有精确限制的时空的多元性。
多孔性的概念用于描述在《扎马》的叙事世界上建立的规则之一:在共享同一空间的人们之间没有明确的、被授命的或遵守的界限。影片从一开始就指出了,虽然有着明显的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但这些并不决定一种不那么相互联系或相互依赖的共存。影片开始,扎马正在偷看一群洗泥浴的妇女,她们亲切地聊着如何用瓜拉尼语说 "黄蜂"。这些妇女中包括卢奇亚娜和马兰巴。正如盖蒙登正确指出的那样,“泥浆掩盖了色素,抹去了白人、印第安人和黑人之间的阶级和种族标记,从而抹去了殖民统治赖以运作的等级制度”(Gemünden, 2019: 110)。 以种族为代表的分裂并不是影片中唯一消退的东西,至少是间歇性的。盖蒙登还指出,散养动物侵入了官方的治理空间,这表明了空间在管理方面存在很大的困难(Gemünden, 2019: 111)。在扎马得知文图拉·普里托被任命至勒马的“惩罚”时,一只骆驼进入了州长办公室的场景就是一个例子。
影片中领土的多孔性通过性活动和欲望变得很明显,其中一个场景发生在卢奇亚娜家的一个社交聚会上,扎马和她的秘书本图拉一起去参加。他们进入时,一群衣着优雅的妇女或跨性别者们在迎接他们。然后,扎马穿过另一个房间,一个马厩。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在为年轻的非洲奴隶胸部作画的人;在后面有一个房间,人们可以进去裸体狂欢,或者说,为此消费,购买性服务。 扎马与这个人交谈,而另一个人从房间里好奇地看着外面的黑人男孩,表明了这个白人男子对年轻的非洲人有性欲望。最后,扎马离开,见到了已经被正式介绍给了其他与会者的卢奇娅娜。


没有绝对的一致性或精确的解释来决定这些空间之间的关系或主体发展的难易程度。这就是影片的另一个叙事规则,它在一个共同体的多样性中展示了性的多样性,并暗示了超越隶属自身社会阶层主体之间的肉体行为。影片巧妙地浓缩在一个简短的场景中,讽刺地描述了一个起源、礼仪、种族和性欲的重叠的空间。与这种戏谑的语气相关,同样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克里奥尔人和西班牙人正式的衣着服饰与他们居住的空间的单一与恶劣也并不和谐。
这些叙事和场景元素有助于马特尔去质疑电影展现殖民历史的传统方式,因为她平铺了分层的社会空间,性欲于其中跨越了阶级的障碍,或至少以一种日常化的方式被实现。就像本雅明在那不勒斯旅行并发现了城市构成的不同层次一样,马特尔的电影展现了扎马所在的社会景观,在逐渐揭示的同时也保留了对主体行为的解释。
这样的设置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这一支配了空间及其社会阶层的多孔性,还看到了在过去与当下之间建立联结点的可能性。这部电影通过模仿与讽刺,再现了一段虚构的历史,于其中思考了日常生活中的性与身份的多样性,模仿、对比了当今的城市空间。
2 ) 丰饶之地上的“丧家之犬”
这部电影看的时候几次想要拖进度条,最终还是没有动手。但过了一段时间,反而时时想起里面的情节,愈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有些意思的。
说“丧家之犬”,按常理说被殖民的土著才应该被冠以这个称谓,当然在电影中也确实是这样,欧洲殖民者把土著人当做奴隶,可以随意殴打,令其劳作。但是电影导演并没有执意让观众在奴隶们身上寻找太多的共情,反而是主角“治安长官”扎马落得个十分悲惨的境地。
贯穿扎马这一段故事最贴切的形容词就是“丧”。主角这个演员胡子拉碴,眼皮耷拉,颓态跃于脸上再明显不过。影片片名ZAMA字幕出现之前就有两个情节,一是主角偷看土著女人洗澡被发现,被追得狼狈不堪。二是工作中审问土著犯人,结果犯人没开口就死了。从一开始起,主角就不断失败。但他不是冲锋陷阵式的失败,没有什么《荒野猎人》等等讲殖民地电影里的欧洲骑士大战印第安野人,而是失败在日常琐事之中。喜欢的房东女儿被侮辱,看着强盗从自己面前跑过。想帮外地来的商人谈生意,结果商人得病死了。去找和自己暧昧不清的财政部长夫人,发现在和别人调情。得不到国王调令,不但被总督骂个狗血喷头,还一直受总督蒙骗。自己住的地方也没有了,真正“丧家”,搬到一家破烂的旅店,老板娘还是个装神弄鬼的神婆,后来又被自己的私生子的母亲冷眼相向。尾声终于想要过把瘾,搞个大新闻让国王认识一下自己,踏上了抓捕传说中的强盗头子维库尼亚·波尔图的旅程,结果还被野生土著抓去玩弄一番,又被强盗头子砍去了双手。纵观扎马的殖民生涯,可谓无依无靠,无亲无故,无所指望,最后还是自己光屁股的私生子救了自己,真是“好像一条狗唉”。
所有的情节,导演都压得很慢,很多固定位置的长镜头,非常沉闷,正如同扎马闷葫芦一样的人物形象,无一例外在强化扎马失败的生活。想要回欧洲结果却只能在南美疲于应对差点送命,对于这些殖民和被殖民普通人来说,殖民地的生活都是一场双输。故事妙就妙在这种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反差设置,颇有耳目一新之感。
最后小船推着水藻前进的镜头美不胜收,南美真是丰饶之地风光无限,也想躺在这样一艘船里虚而遨游,不过当然不能像主角一样,而是要四肢健在。。。

3 ) 谁害怕维库尼亚·波尔图?

马尔克斯笔下有一位上校,他数十年驻守在拉美的殖民地,等待着一笔根本不会到来的退休金,并准备着一次几乎无胜算的斗鸡比赛,56年来,他所做的一切只有等待。

《扎马》看上去与此不无关系,但是,马尔克斯对这位上校的描述是“不放弃尊严的”,这也许是影片中那位名为费尔南德斯的抄写员所创作的内容,我们大可将他看作“拉美文学”的象征。但是,我们无法对驻守着的扎马大谈特谈“尊严”与“非尊严”,由于缺乏一个“典型事例”能够突出这个“典型人物”,他没有能够相依为命的妻子,只有与他生下孩子的情人,甚至没有一个机会,能够被给予一个“变卖家产”的动机,因此就不会有他的“拒绝变卖”而凸显其尊严。
他只是一台机器,一台不断进行着发送与接收的机器,在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看到一系列死气沉沉的“常态化”事件序列,例如主持法庭,批准哑女Malumba的婚事,以及迎接新总督的调任,甚至,在某些极其日常的事件中,“发送者”皆已被内化,这是一台自我运作、自我重复的机器。
(一)囚禁于空间的人
观众与扎马将军共享着时间的不可忍受,延迟的叙事让我们感受到了真正的时间,这种“延迟”很大程度上通过画面的疏离与静观。如同安东尼奥尼用空间囚禁人物,导演卢奎西亚·马特尔同样使用了一个拘禁性质的空间,它看似开放,自然,实际上是封闭的,但《扎马》不同于安东尼奥尼令所有人粘滞其中的现代主义城市空间,在这个看似原始的历史剧里并不缺乏“流动”的意象,原总督可以被调任回西班牙,新任总督可以进入,即使是与扎马发生口角的“治安法官助理”——文森特·普列托也可以离开,所有人都来去自如,除却被囚禁的“行政长官”扎马。

影片的第一个镜头是一个全景:扎马站在海岸,凝视着大海,稍后,它会以不同角度再次出现在银幕上,这里不是出口,而是边界。
这听起来如同福柯“全景敞视监狱”构想,“敞视”这个概念在《扎马》看似被淡化,我们无法看见是什么监视着他,但他确实是被什么东西缠绕着,无法离开。

这个监狱甚至并非处在一个完全已知的空间,它依然留存着一个异质的可怖身份,在飞地之内,一切可能是经验的,而在“他者”中,存在着魔幻的不可化约之物,随时也都会有人突然死去,这是空间的黑洞,以及维库尼亚·波尔图的游魂,稍后,他将再次在文章中出现。
(二)东南亚的驯象者,两个莱尔马
扎马将军请求调任的不是宗主国西班牙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是阿根廷的另一个小城莱尔马,据说,他的家人居住于此。
但这个愿望永远不能实现,而真正意义上的“莱尔马”镇或许与这里同质,即使他被调往,他在莱尔马所应对的,依然是重复着他在这里的发送与接收,“家庭”对于他处境的改变亦是微乎其微。
至于莱尔马,所有与这里的异质均来源于想象层面,扎马将军想象着它的不同,它是弗洛伊德所谓“驱力”的客体,“驱力”意味着永远无法成其所是,它朝向某个客体运动,却永远无法闭合,如同东南亚的驯象者将一串香蕉吊在它的面前,大象越是向前,越是无法达到,假设它的颈部再伸长一点点,就可以达到,但它无法意识到这些,颈部也无法再伸长一丁点,大象的意识和身体所不能及的区域构成了它的自身边界。
由于大象的自身边界以及那一串想象意义上的香蕉,它不得不向前走下去,任由驯象人的操控,也是想象意义上的莱尔马,保证了扎马将军的停留。
欲望的生产性与无法闭合,这是生命得以延续的前提,也是消费社会、商业广告存在的根本。 回到那个经典的画面,当扎马凝视海面时,这个行为被赋予了一种神性的祈祷,那一封信,以及到来的船只都富有了形而上的“拯救”意义,这些延展至发出调任信的主体——西班牙王室,距阿根廷相隔甚远的宗主国,它承担了一个沉默的“上帝”角色,也可能,是前一章提及的“全景监狱”中“敞视”的主体。

如此来看,在美洲大陆,《扎马》回到了中世纪的权力构造,扎马具有信徒—受难者的二重身份,西班牙王室是在场而未显现的“上帝”,那么殖民地总督,即是个体通往上帝之间的政治性阻碍——教皇,阻碍着通往“拯救”的通路,而“拯救”本身似乎并不是真正存在。
所以,在影片中,很少能看到移动镜头,定镜不仅是不可忍受的时间,同样是庄重而神圣的象征,如同中世纪时期的绘画,即使是扎马鲜红的军官服,都已经褪色。
(三)谁害怕维库尼亚·波尔图?——政治的分类学
《扎马》倾向于一种特殊的体认:并不是对宗主国的体认,而是关于扎马个人——某种虚化的身份认同悖论的体认。

这种景深镜头在影片中数见不鲜,扎马是叙事的主体,所以摄影机被放在了他的一边,并将原住民置于后景,甚至在构图中采用人为的视线分割,或许,这样的构图不是政治性的或种族偏见性质的,但是,它明确地揭示出其与当地人之间的距离。
他的身份为西班牙裔,却生于阿根廷,之于双方都存在着相当意义上的距离,这是拉美作为一个第三国家对于自身认同的悖论在个体之上的投射,一个传统—西方世界之间的拉锯战,如果这个故事被放置在当下,那么将无法抗拒“现代性之于个体的异化”这种粗暴的普世化解读,所以,它不得不溯回殖民史的源头,就像弗洛伊德主义者主张回归早年时期寻找病灶。
扎马生来被放逐,而不是主动的“殖民”行为,所有关于他的传说比他本人走得更远,他从“他者”的讲述中构成自己。
在“奥尔连托人(东方人)”的叙述中,他是“无需拔剑即可伸张正义的”、“不会隐藏他的义务的”“行政长官”,在这一幕中,一个反打镜头揭示了扎马的反映,如同等待“被本质化”的焦急以及对镜中我的沉溺。

“行政长官”是一种身份,无法逃避的身份,他虽然没有殖民者的威严,但也不能像文森特·普列托一样轻易地被调任,从这种意义上,他又类似与他有隔阂的原住民,被框定在这块土地上自我重复,这是在他身上所体现的“第三国家”特质。

而维库尼亚·波尔图则是另外一种,他可以是任何姓名,因为其姓名与其所指是随机组合的,甚至没有隐喻,他提醒我们存在着秩序之外的危险而不可化约之物,并将它们所有归化入这一符号之下。

当破衣烂衫的扎马持刀走向所谓“维库尼亚·波尔图”时,出现了罕见地出现了一个近景跟拍,维库尼亚,或者说捉拿维库尼亚是被影片延迟的最终叙事,它依然属于发送—接受,只是在叙事中加入了助动者与逆动者。

这个姓名政治性地为扎马赋予了“行动”的意义,政治是一种权力的分类学,或是命名学,在意识形态中,一个威胁性的“他们”的存在相当重要,因为没有比这再好的方式来确立,理解“我们”的概念,“他们”是一个垃圾桶,吞住认知上和想象意义上的黑洞。
维库尼亚·波尔图不可能抓住,相传他已经被处决,新任总督身上佩戴的耳朵即是最好的证物,也有人说他还活着,所以不得不发动扎马一行人去追击,但他不可能被抓住,所谓“维库尼亚·波尔图”只存在于理念之中,一切可见之人皆为此理念的拟像。

结尾,移动镜头再次出现,摄影机缓缓前推,雨林明亮的翠绿色调与扎马将军被割掉双手,奄奄一息的处境形成反差,它迫使观众回到影片开始之前,重新审视那个关于鱼的寓言,看清扎马的所作所为真正带领他走向的是什么,“活着”这扇门本身是敞开的,而现在,死神即将把它关上。

参考文献
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陶玉平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5月第1版
Paul Schrader :Transcendental Style In Film,De Capo Press,1988-8-22
斯拉沃热·齐泽克:《享受你的症状——好莱坞内外的拉康》,尉光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
4 ) [Film Review] Zama (2017)

Lucrecia Martel’s long-awaited fourth feature ZAMA is a period drama about the downfall of a Spanish empire functionary in the end of 18th century, her first attempt of visualizing a story from a literature source, Antonio Di Benedetto’s eponymous existential novel.
Don Diego de Zama (Giménez Cacho, bringing about a gravely intense concretion of mental exertion and physical resignation) is a Spanish magistrate in a South American colony, who is so cocksure that soon he will be transferred to Lerma and reunited with his wife and children, he barely conceals his peremptoriness, in time it will escalate into a brawl with his subordinate Ventura Prieto (Minujín), ironically, in the aftermath, it is the latter would be immediately reassigned to Lerma, and Diego’s transfer plea continues to be bogged down in the red tapes and the perverse obstruction of a new governor.
In a post-colonial epoch, it has become a wonted bent for us to cogitate on the world’s colonial past with a sober sensibility of censure and contrition, Martel follows suit, effectually extends her uniquely elliptical story-telling methodology into anatomizing Zama’s quotidian absurdity and displacement, often heightens her unorthodox compositions (notably for her astute attention of the negative space) and leaves the spotlight right off the camera, the effect aims for a less direct impact upon viewers and allots us time to ruminate on these moments’ often mystifying undertow, most prominently, the incommunicability between two disparate civilizations and the unuttered defiance of the local slaves and indigenous tribes.
This approach becomes a magical antidote to the spoon-feeding narratology, viewers tend to be more concentrated on the less specified happenings and discernible to the particulars (not least a llama swanning in the background in one close-up shot), what is more extraordinary, Martel knows the proprieties, she never pushes the limits to the extent as a deliberate provocateur and expeditiously cuts away from dramatic sequences, then affixes them with what happens after in total composure, also, acute auditory hallucinations are dexterously integrated to elicit an uncanny feeling that complies with the otherness percolating through Zama’s increasingly disoriented sensoria, he sees ghost, hears other people’s thoughts and loses his bearings?
Martel cogently substantiates that is a lose-lose situation for both the colonizers and the subjugated natives, a deep-seated defeatism permeates the whole film an attains its crescendo in the phantasmagoric third act, when a disenchanted Zama joins a ragtag group of bounty hunters trying to capture a mythologized figure Vicuña Porto, only finds out that after their delirious baptism of fire, Vicuña might or might not be right among them, a coup de maître of cinematic metafiction about self-delusion and nihilism.
To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ZAMA bewitchingly reassures us Martel is a sui generis tastemaker in today’s cinema-scape, an acquired taste, maybe, but once you are onboard, there will be elation aplenty.
referential entries: Martel’s THE SWAMP (2001, 7.4/10); Pablo Larraín’s NERUDA (2016, 7.3/10).

5 ) 内容
扎,出生在南美,西班牙王室人员等待一封信从国王授予他转移到一个更好的位置。他的处境是微妙的。他必须确保没有遮蔽他转移。他被被迫顺从地接受每一项任务委托给他的历任来来去去,他呆。当然,王信从未到来,和当扎注意到他已失去了一切等待,他决定参加一个聚会后一个危险的强盗去的士兵。也许这种方式他可以得到国王听到他。扎叶到遥远的国度居住的野生印度人,但他们都轮流出后会他的士兵之一的强盗。扎俘虏和 Vicuñas 的男人想判他死刑。正如他现在免费从他的被希望转移和促进,知道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他发现,他唯一的愿望是活着。
6 ) 富有强烈实验色彩的历史题材
阔别将近10年的阿根廷女导演,依然我行我素地坚持一如既往的作者风格,交出一部风云诡谲的作品。我想用实验历史题材来作为归纳这部多重主题探讨的作品,常规的西方历史戏我们看得多,要么是你死我活勾心斗角的宫廷大戏,要么是金戈铁马一腔热血的战争诗篇,再就是物欲横流色情挑逗的爱恨情仇。然而,在马特尔镜头下,难以见到这些千篇一律的套路。导演首次改编文学作品,描述的是一位生于南美殖民时期的西班牙治安官,他一直希望调离这个殖民地处境,却最终身不由己地走向荒诞的结局。 宏大的历史叙事在油画般的影像里销声匿迹,历史不再是奔涌前进的洪流,反而是碎片化的事件堆砌,只剩下男主人公在困扰心思的日常细节里原地周旋。“时间”这个历史题材里极为关键的因素在强烈的作者风格里显得迟缓,甚至停滞不前。这似乎与主人公在事业、家庭乃至命运上的遭遇息息相关,他屡屡面对挫败,难以从繁重的官僚体制与自视甚高的身份特权中抽身而出。他看起来很像卡夫卡著名作品《城堡》里的K,对自己能被调离殖民地深信不疑,怀着不可名状的傲气与轻浮(从他对待下属与贵妇人的段落可验证),渐渐才发现自己只不过是被历史淘汰的沙子。而且他深入骨髓的殖民者思维也在不断推动着他最终走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除了碎片化的历史观,导演更着重声音的处理,用实验色彩鲜明的手段来打破传统历史题材的声乐风格。常规历史影片,观众听到的往往是挑拨情绪的意大利歌剧,或者是烘托出宏伟氛围的管弦乐,但在马特尔的这个实验历史故事里,选用的配乐却是与王家卫的《阿飞正传》里如出一辙的夏威夷四弦琴声,不断营造出南美大陆的神秘梦幻气息。 除此之外,观众更能清晰地听见昆虫鸣叫,小鸟与马匹的叫声,无数来自南美森林的声音,以及更多来历不明的诡异声响。这些声音有的是为勾画特殊的殖民地环境,更多的则为刻画主人公心理变化所用。比如在好几个场景里,主人公突然出现幻听,他周遭人物的话语明显隐去,却浮现出阴沉诡异的声音,如此例子在影片后半部主人公不断陷入困境时表现得更为显著。这种将外界环境声响赋予叙事意义的处理手法,可以说是马特尔的独门秘笈,在处女作《沼泽地》及之后的几部作品里都有出神入化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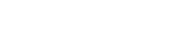




















相比三大主竞赛单元那些还在美学和派系范围内另类求新的导演,还是卢奎西亚·马特尔这样的导演走的更远,在她的电影里,你熟悉一切电影技巧,但乍看她的片子,还是会无所适从,她已经差不多讲叙事功能剥离干净了,你和片中的主人公一样,身在历史中,什么都看不清,只是被事件和生活推着往前走。
扎马困于殖民地,观众困于电影院。◎SIFF21
配乐一秒出戏阿飞正传。。。。
惭愧的说,20分钟后,我就放弃了对影片的阅读和理解。当然,这绝对是我自身能力的不足。
请卢奎西亚·马特尔、凯莉·雷查德、阿尔伯特·塞拉、利桑德罗·阿隆索组一个新电影联盟。
失敗,即是不斷剝奪。是沒有救贖也沒有出口。拿走故鄉,曖昧,居所,再拿走權力,身份和肢體。人慢慢跌入「原始」和「未開化」,最後只剩生存的慾望。從一個給別人耳光的人,成為被救助的人。失敗,真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看完就想立即重看。片头的导语已经将全片的情节交代完整“水迫使鱼离开水域”,电影将时空细节模糊掉,事件也去掉首尾平生诡谲,观看过程就是与Zama一同泡在这漫无边际的水中。导览人说Zama像是荷索影片里的Kinski。都是偏执且无止境的探险。
马特尔对自己身在其中的这个阶级的作茧自缚显然既非恨之切,更未爱之深,而她潜心学术一般的精确剖析看一次两次或许还有所触动,三次四次则无聊之至。至于那个视线之外的声音世界…在引入更多景深之后似乎除了画框都无法容纳的Ego之外也意趣寥寥。
能了解导演的创作意图,对扎马的无能表现富于同情和嘲讽,批判殖民主义和随之而来的奴隶制,又集中在政府官员逃离他们被指控压制的文化。但编导刻意避开现实,不断情景暗示,试图建立了一种神秘狂热的氛围,致使叙事割裂,主题支离破碎,观众难以进入这个外来殖民世界。也就美术和声音是种享受。
wow
感觉核心台词说出来的时刻完全没有那种累积后爆发的冲击力
Alonso在Jauja里把这种美和荒诞拍活了,而Martel这部更适合挂起来。3.5
两次睡着 不过导演说我们都在看伟大作品的时候睡着过 所以不要不好意思
银幕里的扎马望向尽头,渴望离开殖民大陆;银幕外的观众不时看表,希图从影厅解脱。伴着迂回海浪、潮湿苔藓、听不懂的族语、吱吱呀呀的扇风,原始而神秘。这里时间悠长,包着玻璃杯的报纸比送来的报纸还新;这里故事惆怅,断手断脚在热带雨林涂满粉红染料。这是一种奇妙的观感,你我都如扎马一样焦灼。
背景设定在南美殖民的奴隶制时期,摄影复古如油画,但创作者似乎不想再现历史,加入荒诞元素,把男主命运和异域奇观、时代背景紧连在一起。戏谑的配乐和服装妆容使得电影戏剧感极强。完全被剧照吸引来看,因知识有限,我只看到了身在野蛮向往回归文明却不可得的悲,但似乎无法解读深层次的东西。3.5
可视为《百年孤独》前传,拓荒新世界,梦想荣华富贵的个体扎马们就像被水排斥的鱼,被遗忘在大历史缝隙的原地里,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哥伦比亚或阿根廷的祖先,游离在美洲上空眺望永不可返回的欧洲故土。身份的质疑源于两不靠边的身处——存在与虚无、原住民和殖民者、记忆与遗忘。魔幻现实主义源于对命运所开玩笑的反击,自此注入拉美人的血液,Antonio di Benedetto与世隔绝,自我流放的孤苦被导演用镜头语言展现无遗,技术上也有匠心独运之处,大量近景的凝视,远景的眺望反衬出对回家的渴望,最终还是被卡在大河入海处。OST真像王家卫喜好那种。
“生而不能死的神,他的孤独是残暴的”;被杀一千次的波尔图,等同于永无可能等来的信件,终生陷困在泥淖殖民地的戈多,迷失在历史的虚无里,行走在梦一般的暗夜里,游弋在原地的鱼一辈子也无法企及陆地,处于殖民统治者与原住民夹缝中的身份迷失与焦灼逃离;音效很赞。
#SIFF2018#毫无消费南美元素之嫌,而是充满魔幻土地中自发生成的生命力;囿困于命运的人,如囿困于水的鱼,“鱼的一生都在被水排开”,于是看见扎马在命运的激荡水流中几几起落沉浮,从前半部分迷离氤氲的迷茫气氛里走出,走过惊险与壮阔的丛林,走向明亮的碧海蓝天下的平静死亡。
Jauja的热带互文,抛弃叙事的蛇之拥抱,现在再看这样混沌潮湿且处于远距时间的影像已完全无法共情,残留给庸众如我聊以解烦的简单体制对照,弃民之于弃民的驱逐,和带着距离感的黑色幽默。
言语无法形容的伟大。一个人,困在时间和等待的夹缝中,即使摇动记忆也唤不回磨蚀殆尽的热望,层叠反复的曲调越弹只越悲伤,长夜总要燃尽,倒不如松开手中流沙,容自己再梦一场。201806SIFF重看。20190504重看x3 其实zama周围的一切对他都是敌意的,他被四面紧逼的高墙死死压住再也不能喘息,无论屈服与不屈服都是徒劳,言语的功能全面断裂,到最后他甚至不再知道自己在战斗什么,这样极端的downward spiral或许难以相信,但有人真的就是如此不幸。